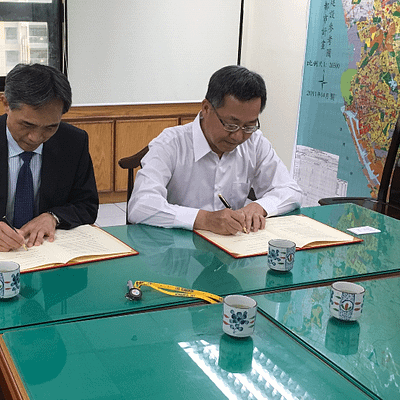首頁 新聞 尼泊爾山難》「我若不這麼做,火車就無法駛進沿著平原開展的夜色裡」劉宸君的最後公開遊記
尼泊爾山難》「我若不這麼做,火車就無法駛進沿著平原開展的夜色裡」劉宸君的最後公開遊記 台灣籍的梁聖岳和女友劉宸君3月在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區失蹤近50天後被找到,劉宸君已無生命跡象,梁聖岳則意識清楚。(取自Ganesh Himal Tourism Development臉書)
東華大學華文系學生劉宸君日前在尼泊爾山區遭遇山難、不幸逝世,她的親友在臉書上的協尋呼籲,也都化作了悲嘆與唏噓。今年2月7日,劉辰君在印度的西爾恰爾紀錄了當時的所見所聞,以及跟男友梁聖岳在西孟加拉邦與阿薩姆邦的經歷。在這篇最後公開發表的臉文中,我們也得以窺見年僅19歲的劉辰君作為壯遊世代的視野與心思。
大約一週前,聖岳連結在單車後輪的行李拖車花鼓嚴重損壞,在印度無法維修,只能等待一位三月將和我們在尼泊爾會合的朋友從台灣帶來新的輪組,才能繼續倚賴單車移動的行程。事實上,我們很可能都非常慶幸這件事發生。西孟加拉邦實在不是個適合騎單車的地方:每天你吸入大量的霧霾,車輛瘋狂的駕駛技術、一長串音色詭異的喇叭聲令你完全無法理解自己到底置身何處,覺得生命都被扯成一串詭異的音符。當你停下自己的單車,身邊會瞬間擠滿圍觀的人群;你完全不曉得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就像剛拔完草卻下了一場大雨,無法理解雜草又是什麼時候長出來的一樣。
這陣子我們得仰賴火車進行移動。出國前,我確信我的Masi CX旅行單車能夠帶我穿越任何地方,到了印度卻時常不斷質疑這件事。有時我被困在車流中,覺得自己根本騎不出置身的公路和街道;紮營通常是困難的,必須往前不斷推進,直到找出不會亂開價的旅社為止。往前推進時世界無止境的運轉,所做的一切彷彿都回到某個原點。我們以極其疲累的語氣強撐著臉上的微笑,回答每位圍觀者的問題,心中不斷祈禱能夠儘快擁有自己的空間。但和其中某些人的眼神對上時,我又會突然覺得自己正在介入、甚至破壞什麼;我情願自己從未抵達這裡,也情願自己不曾擁有這部單車。
鐵軌將某部分人的生活一分為二,這一岸和那一岸的生活是相互對稱的。你能夠在鐵軌兩邊看見正在曬晾的鮮豔衣物、凌亂的被褥、煮食的炊煙。從古瓦哈蒂到Lumding的路途上,我甚至看到鐵軌兩邊的人們都撿拾了印有甘地頭像的廣告看板做為蓬屋的建材,宛若一個堅實、嚴密的社群。當然,鐵軌上也會有零星的小小社群,在加爾各答附近移動的區間車上,有人把整個沙發搬到鐵軌上,她就坐在上面曬太陽。火車接近時會對這些人按喇叭,他們就自動移開鐵軌上的家當,等待火車通過,再回到鐵軌上繼續生活。
Second class(二等車廂)的走道時不時會有人來回穿梭,販賣任何你的想像能觸及與無法觸及的物事。賣礦泉水的小販會把箱子扛在頭上,賣某種咖哩豆的小販則是一手提著裝滿豆子的鐵桶,另一手拿著非常薄的塑膠容器。如果你要買一份那種豆子,他會把鐵桶放在你面前,把豆子舀進塑膠容器裡頭給你。坐在我們對面穿著傳統服飾的姐妹,其中一位還穿了鼻環,用名片那類較硬的紙剪成的紙條舀那些豆子吃。我們也碰上不知如何面對的時刻:一位流鶯直接在走道對聖岳提出邀約。遭到拒絕後,她帶著她的驕傲離開。那是種輕佻、卻絕對不容被侵犯的氣息。
(相關報導:
【互動新聞】尼泊爾山難情侶被發現處 距離喜馬拉雅山主峰將近200公里
|
更多文章
)
火車駛入森林,穿越平坦的田野。在火車上,隔著一個距離看待事物的時間變多了。我並不因此認為自己正在遠離什麼,儘管真正的接近是不可能的。「穿越」意味著暗示的發生,在池塘裡用力撒下棕色漁網的婦人可能是一種暗示,停在檳榔樹叢中的鐵馬是另一種。背著弓箭的父子,往森林的方向走去。
我們打開平板電腦裡的離線地圖。這列擁有30幾節車廂的列車前半部的車廂已經開始左轉了,後半部卻仍在右彎。離線地圖紀錄著列車行徑路線的變遷:原先隧道並未被打通,列車必須拖曳著曲折的軌跡,繞過一座山頭。甚至最後我們推論那條鐵軌很可能能夠通往緬甸,因為舊鐵路在地圖上顯示的是東南亞規格的米軌,而非印度鐵路常見的寬軌。在臺灣的時候,我們曾經在廢棄的舊隧道裡頭紮營。那時我們的呼吸一定變得謹慎而緩慢;我們或許真的以為,火車的靈魂會從那個迷幻的深處衝出來,但卻不曾發現,可能是自己被吸進去了。
前幾天,我們悄悄回到一列暫時不會開動的火車上,在火車裡渡過一夜。
大約晚間十點左右,我們抵達Alipur Duar 站,原本打算在車站睡一晚,等待隔天清晨四點開往古瓦哈蒂的班車,卻被車長告知我們能夠留在車上,清晨四點這輛列車會繼續開往古瓦哈蒂。重新走回列車上,電源全數被切斷。世界並未跟著死去,我聽見遠處傳來的汽車喇叭聲、火車調車移動的清晰聲響、巨大的電子音樂聲使我明白自己仍然與某個世界極為接近,但卻被隔在另一個世界裡。
我們在空蕩的車廂中為了非常小的事情吵了一架,與其說在旅行中,任何微小的事件都能夠使接下來的旅途變得令人難以忍受,我寧可將我們的爭執視作為了避免旅途的重量變得太輕,得用這樣的方式使重量回復。他想躺下,身體卻十分僵硬,而我也在他對面的座椅上無法動彈。隨著時間過去,他緩慢地從背包中摸出一個非常薄的塑膠袋,拿出一截細長的物體,直到打火機敲擊的聲響傳來,我才知道那是他在泰國買的蚊香。火團包裹住蚊香的前端,吹熄後只剩下火星,煙霧一絲絲地飄升。他把蚊香卡進窗縫,關上的窗戶上面有百葉窗式的橫紋,但肯定也有垂直的結構。
(相關報導:
【互動新聞】尼泊爾山難情侶被發現處 距離喜馬拉雅山主峰將近200公里
|
更多文章
)
我站起身,往他那張椅子的方向走過去。坐下來後,我將原本深吸的一口氣吐出,才真正開始流淚。我必須用盡全身的力氣節制自己的情感,才能允許自己流淚。我若不這麼做,火車就無法駛進沿著平原開展的夜色裡,而我也無法和他在車廂裡再多待一些時間了。
更多新聞請搜尋🔍風傳媒
目前贊助金額 NT. 6.16K
想要一起表達支持這篇文章?
贊助文章
更多文章
「不是威脅」!徐國勇:若立委認為前瞻不需要,可以大聲說 行政院發言人徐國勇今天表示,若有立委認為選區不需要前瞻基礎建設,可以大聲講出來,像高雄的軌道建設或新北水環境建設,若立委認為不需要,可以提出來,行政院會檢討。立法院昨天在激烈衝突中初審通過前瞻基礎建設條例草案;同時,昨天行政院政務委員吳宏謀在民進黨中常會報告前瞻計畫中的水環境建設後,總統蔡英文認為行政部門論述、宣傳不足而動怒。徐國勇上午主持行政院院會後記者會,他在會中澄清,蔡總統並沒有責怪吳宏謀或行政院,而是因為吳宏謀將報告重新整理後,蔡總統認為論述方式不錯,可加以推廣。對於外傳行政院長林全今天將再次親自出面說明前瞻基礎建設,徐國勇表示,林全並沒有安排此行程,政院也從來沒有說過林全要開記者會,只是有人建議林全應親自說明,但因已有其他行程安排,時間挪不開。
「當南風吹來六輕的酸臭味道」,台大教授找到原因 六輕附近居民常抱怨空氣有酸酸、臭臭的味道,台大公衛學院副院長詹長權研究發現,這種酸臭味推測是高濃度的甲酸氣體,是石化工業污染物之一。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詹長權團隊,在西元2014年至2016年接受彰化縣衛生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委託在彰化縣大城鄉和竹塘鄉執行研究計畫。今天上午在台大公衛舉行記者會發表研究成果。研究團隊在記者會播放大城鄉台西村居民的心聲,其中一名居民表示,日前晚上睡覺因天氣熱,沒關窗,但睡到凌晨2時許,就聞到空氣有臭味、酸味,「醒來感覺到這是六輕的味道」,趕快把窗戶關起來。詹長權表示,他長期在六輕鄰近區域蹲點研究,居民很常抱怨不管是白天還是晚上,空氣不好聞、有酸臭味,但一直都不知道這種臭味的來源。
南韓總統大選》還有兩週投票 文在寅支持率狠狠甩開安哲秀 南韓總統大選將在5月9日正式投票,海外韓籍人士從25日到30日也已經開始投票作業。不過根據27日發布的最新民調,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以44.4%的支持率,大幅領先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22.8%)。而且文在寅在所有大選區、50歲以下民眾、左翼中間選民通通領先,似已勝券在握。
陋習一堆!人頭黨員何解?郝龍斌:未來黨主席選舉採計民調 國民黨主席選舉激戰,發生人頭黨員爭議。國民黨副主席郝龍斌27日指出,黨主席的社會形象與支持認同度很重要,因此,他主張黨主席選舉要採計一定比例的一般民調,同時,提高新黨員的投票權門檻,應該可以解決很大部分人頭黨員的問題。
反年改520抗爭恐干擾國中會考 李來希:國家這樣考上又怎樣! 國中教育會考將於5月20、21日登場,但反年金改革團體預計在當天上街抗議,有民代、家長就呼籲希望抗爭別選在周遭,以免影響考生權益。全國公務人員協會理事長李來希今(27)日批評,「不過就是個考試嘛!有這麼重要嗎!」他也大罵,「國家這樣繼續下去,你考上了又怎麼樣?」
別再嫌燙青菜很難吃啦!3個科學汆燙小技巧,一把10元蔬菜也能變身神級美食 所謂的「燙」,就是將食材放進沸騰的熱水中加熱。這種烹調方式可去除食材原有的嗆味、澀味、黏液等,使食材更美味,蔬菜燙過之後會變軟,蛋、魚、肉類燙過之後蛋白質會變硬,可品嚐到有別於生食的口感。熱水的分量與溫度,以及有沒有蓋鍋蓋,都會影響食材燙熟後的色澤及口感,因此汆燙時切記需隨時視食材的性質、想製作的料理、家人的喜好,運用各種方式進行調整。
「尿液中重金屬污染物高於其他村」,台大研究:台西村民癌症發生跟六輕相關 台大公衛學院研究發現,距離六輕較近的大城鄉台西村、頂庄村居民尿液有較高重金屬污染物,且台西村居民癌症發生和六輕營運有顯著相關。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教授詹長權團隊,在西元2014年至2016年接受彰化縣衛生局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委託,在彰化縣大城鄉和竹塘鄉執行研究計畫。今天上午在台大公衛舉行記者會發表研究成果。研究發現,距離六輕工業區較近的大城鄉台西村、頂庄村(平均約8公里)居民尿液中的釩、鉻、錳、鎳、銅、砷、鎘、鉈、鉛等重金屬和1-羥基芘(多環芳香烴的代謝物)等10種污染物濃度都高於遠離六輕工業區的竹塘鄉(平均約20公里)居民;氯乙烯的代謝物硫代二乙酸濃度也高於大城鄉其他村(平均約10公里)居民。
全球財經掃描:美稅改蝸行牛步,政府關門在即,市場轉趨保守 昨美國財長Mnuchin及總統經濟顧問Kohn一如預期宣佈了稅改計畫,內容包含下調企業稅至15%,並簡化個人所得稅級距至3個,稅率分別是35%、25%、12%,提高一倍標準扣除額,另提及pass-through(獨資、合夥、小型企業等)將轉為課15%企業稅、並將調降匯回稅與廢除房地產遺產稅,上述內容與競選時期所提出方案相比,仍然缺乏完整細節,對於資金來源的規劃也付之闕如,財長強調該計畫為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計畫,但也說明此些僅為核心原則,而由於這些內容對於市場並無新意,加上日後恐遭到國會修改,最終何時推出、何種型態推出不確定性仍高,致市場氣氛由樂觀轉趨保守。整體來說,我們認為此次Trump急於宣佈一些稅改重點方針,主要是希望於百日新政到期前可給大眾一個交待,維持其對於選前承諾有所行動,Trump自就任以來一貫的模式為有做就好,有否達成或效應如何則是另一件事,因此目前稅改的進度與宣佈之前應無太大差異,非一蹴可幾,8月國會休會前難通過,市場或仍將先經歷一定動盪。
遊高雄宿一晚 市府送上「住遊購」三大好禮 瞄準國內外自由行旅客,高雄市政府觀光局結合旅宿業及商家,約70家觀光業者,自5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推出「宿高雄一晚送你住遊購」優惠專案,凡到高雄旅遊,只要入住專案配合之飯店或旅館一晚,就可享受「住遊購三大康」,含旅宿、免費遊程及購物優惠等多項方案,希望吸引國內外旅客呼朋引伴到高雄觀光。
「台語很溜是你的特色!」曾是矯正學校學生,如今他用台語導覽名畫,自信重生 劉昶佑長得高瘦黝黑,笑起來帶著一絲靦腆,有點害羞;但是只要他一開口,用草根性十足的流暢台語來介紹「維納斯的誕生」,馬上成為全場最令人驚豔的那一位。來自高雄的劉昶佑並不諱言,青少年時期有過一段荒唐歲月,心總是靜不下來,想不到因為全心投入藝術導覽,為自己創造成功經驗,才從黑暗中找回重生的力量。
BT美股五分鐘:川普稅改出爐,標普看漲2450 大家好!今天是2017年4月26號,星期三。今天美股三大指數變化不大,截至收盤,標普指數微跌0.05%,報2387.45,道瓊斯指數小跌0.1%,報20975.09,納斯達克指數平盤收盤,報60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