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們都同意,人類社會基本上需要某些限制與規範,接下來馬上面臨的問題是:「應該採用誰的規範?」
美國二十世紀末建立的富裕、自由、多元的社會裡,「文化」一詞總是與選擇聯想在一起。也就是說,文化是藝術家、作家及其他有創意的人根據內在的聲音創造出來的。至於比較不具創意的人,文化則是他們選擇去消費的東西,不管是藝術、美食或娛樂。美食常被視為文化的一種代表(雖然只是很表層的意義),尤其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美食。能夠在中國菜、義大利菜、希臘菜、泰國菜、墨西哥菜裡自由選擇,這就是多元文化的意義。當然,多元文化還包括更嚴重的內容,就像伍迪.艾倫在電影中得知自己罹患癌症末期,開始從佛教、訖里什那教派、天主教、猶太教中瘋狂尋找一種心靈的慰藉。
我們更學會了在做文化選擇時絕不評斷高下。在道德層級裡,寬容是最高的美德,依據自己的道德或文化標準評斷他人則是萬惡之最。品味是沒有道理的,就像每個人喜好的食物不一樣,不同的道德規範根本無高下之分。這種互相尊重的觀念似乎已經是社會的共識,不僅是主張多元文化的左派人士大力宣揚,即便是將所有人類行為都化約為追求個人「偏好」的右派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也同樣支持。
為了避免文化相對論的問題,本書的重點不是放在大型普遍的文化規範,而是足以構成社會資本的小型規範。「社會資本」可定義為促使團體成員合作的共通非正式價值或規範。當團體成員預期其他成員的行為都是誠實可靠的,自然就能彼此信賴,而信賴是使任何團體或組織運作順暢的潤滑劑。
擁有相同的價值觀與規範並不必然就能產生社會資本,因為這個價值觀可能是錯的。例如義大利南方確實存在強烈的社會規範,但這裡也是世界上最缺乏社會資本、人與人之間最缺乏互信的地方。社會學家甘柏塔(Diego Gambetta)說過一個故事:
一個退休的黑社會老大回憶年幼時他的父親(黑手黨員)要他爬到牆上跳下來,承諾會將他接住。起先他不肯跳,經不起父親一再催促,最後還是跳了下去―結果摔了個鼻青臉腫。他的父親藉此教導他一個道理:永遠不要相信別人,包括你的父母。
黑手黨以極嚴格的內部行為準繩著稱,每個人都可以做到一言九鼎。但這套規範僅適用於路手黨的小圈子,整個西西里社會盛行的規範是「盡可能占別人便宜(自家人除外),否則倒楣的是自己。」有時候甚至連自家人都不太可靠,就像上述故事所說的。這樣的規範當然無助於社會合作,對廉能政府與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更是見諸各種研究。義大利政界貪汙問題嚴重,尤以南方為最,事實上這也是西歐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能創造社會資本的規範必然包括誠實、善盡義務、互惠等德性。這些德性恰與清教徒的很多價值觀重疊,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裡便認為,清教價值觀對西方資本主義發揮了關鍵影響力。
每一個社會都有社會資本,真正的差異應該是所謂的「互信範圍」(radius of trust),只有範圍裡的人始能分享誠實互惠等社會規範。家庭顯然在任何社是社會資本的重要來源,美國人儘管對自家的青少年子女多有微詞,談到信賴與合作事業還是寧可選擇自家人。這也是為什麼多數事業開頭都是家族事業。
但家庭的凝聚力各國不同,與其他社會凝聚力相比較家庭的重要性也不同。有時候我們會發現,信賴與互惠規範在家庭內外的強弱似乎是呈反比的,內強則外弱,反之亦然。例如中國與拉丁美洲的家庭凝聚力很強,但不易信任陌生人,公共領域的誠實與合作程度顯得較低,結果便造成派閥主義與貪汙腐敗。韋伯認為,新教改革最重要的意義不是鼓勵個人重視誠實、互惠、節儉等美德,而是使這些美德首度得以在家庭之外被廣泛實踐。

成功的組織未必都需要社會資本,也可建立在正式的協調機制如契約、階級、憲法、法律體系等。但非正式規範可使經濟學家所謂的交易成本大幅降低―亦即監督、訂約、裁定、執行正式協議等的成本。在某些情況下,社會資本也有助於創新與應變。
當然社會資本的效益絕不限於經濟層面,也是創造健康公民社會的關鍵。所謂公民社會,是指家庭與政府之間的各種組織。自柏林圍牆倒塌後,前共產國家對公民社會產生很大的興趣,一般也認為這是民主政治成功的要素。複雜的社會裡有各式各樣的團體,社會資本使不同的團體得以組織起來護衛自己的利益,以免被強勢的政府忽略。很多學者注意到公民社會與自由民主的密切關係,已故的蓋爾納(Ernest Gellner)甚至認為自由民主是公民社會具體而微的表現。
專家在討論社會資本與公民社會總是充滿正面的形容詞,事實上兩者也不盡都是有益的。任何社會活動不論好壞都需協調。柏拉圖的《理想國》敘述蘇格拉底與朋友討論正義的問題。蘇格拉底指出,即使一群搶匪對待彼此也會有正義感,否則就無法合作犯案。黑手黨與三K黨是美國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兩者都具有社會資本,但都對廣大社會有害。再就經濟層面而言,團體協調是生產活動的必要條件,但隨著技術或市場的改變,協調方式往往也必須隨之改變。過去適用的社會連結方式對現在的生產活動可能反而是阻礙,就像一九九○年代很多日本企業的情形。如果我們再繼續上面的經濟學比喻,社會資本也會有老舊的時候,屆時就必須從國家的資本帳上折舊。
雖然社會資本可用在不利社會的方面,而且有老舊的可能,但一般觀念總認為社會資本就是好的。事實上,實體資本也不見得都是好的。實體資本不但會過時,還可用以製造槍枝、不良藥物、品味低俗的娛樂等。但社會自有法令約束人們製造出有害社會的東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社會資本的使用不會比實體資本更不堪。
抱持上述觀念的人不在少數。第一個使用「社會資本」一詞的是漢尼芬(Lyda Judson Hanifan),在一九一六年用以敘述鄉村的學校社區中心,其後有傑柯斯(Jane Jacobs)的經典作品《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文中談到都市中舊式綜合用途的社區有綿密的社會網絡,形成極有助於公共安全的社會資本。一九七○年代則有經濟學家勞瑞(Glenn Loury)及社會學家萊特(Ivan Light)以此分析大都市中心貧窮地區(inner-city)經濟發展的問題。他們認為黑人不像亞裔或其他少數族群在自己的社區裡有很強的信賴與社會連繫,這也是為什麼黑人在中小企業方面的發展很有限。一九八○年代,受到社會學家柯曼(James Coleman)與政治學家帕特南(Robert Putnam)的影響,「社會資本」一詞再度被廣泛運用,後者的論點在義大利和美國更引起激烈的辯論。
有一個人從未用過社會資本這個名詞,卻可能是闡述這個觀念最清楚的人,那就是法國貴族兼旅行家托克維爾。托克維爾在《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裡提到美國與法國一個極大的差異,即美國人展現出豐富的「自發結社」,人們習於為各種或輕鬆或嚴肅的目的形成自願組織。美國式民主與有限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為美國人善於為公民或政治目的而連結。人民既有足夠的自我組織能力,政府不須用由上而下的層級形式維持秩序,人民更能從自我管理中學到合作的習慣,並將這樣的習慣帶入公共生活領域。我想托克維爾一定會同意我們的結論:沒有社會資本就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公民社會就沒有成功的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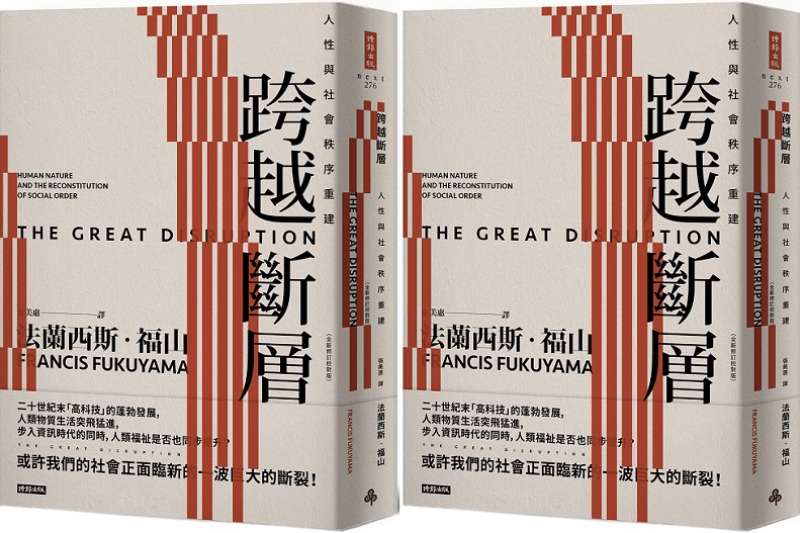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史丹佛大學國際研究所教授,兼民主、發展與法治中心主任。本文選自作者著作《跨越斷層:人性與社會秩序重建》 (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