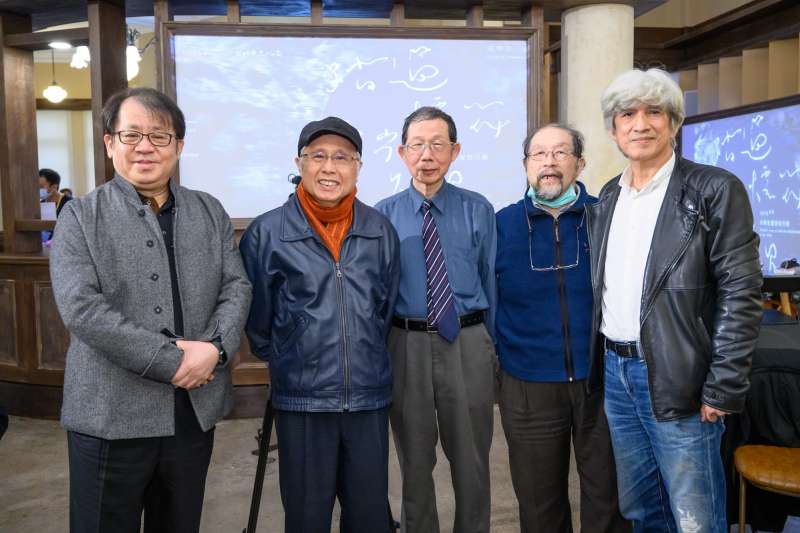「丘延亮」在圈子裡不同時期、不同人有不同的稱法:阿肥、老肥、肥哥、肥公,以下簡稱「肥」。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收到肥來信,要我有空幫他寫序,近四〇年的老哥們,不可能說不,自己三本書稿拖了很久,只能丟下進行的寫作,接下這個活兒,九十萬字!壓力很大。過去十多年他的「經紀人」(皮條客)阿三,過一兩個禮拜就傳來一些有的沒有的嚴肅故事,陸陸續續零散的讀過,任何人要在一個月內好好消化三大卷,還是很難。吃奶的力氣用上,兩週讀完,除了更知道肥與其筆下的時代,要說什麼呢?
我一九五七年出生,六〇年代還是指南山下的快樂的白痴,童年記憶與《台北之春》交織重疊的是身經湯系大別山戰役的父親,父親曾任職南京總統府衛戌司令部,管思想,在杭立武先生邀請下調到教育部移送最後一批故宮,負責安頓「流亡學生」,家裏常來了一批批陌生年輕人,搞不懂怎麼回事,文中才看到這麼多故事。還有秦松聲如洪鐘的父親大漢秦嶺在桃園中學教書,是家父安徽同鄉的酒友,後來我們口中的大哥能保釋赴美耳聞國防研究院一期的父親大概出了點力;陳伯伯(雪屏)是家裡常客。

後來才知道袁世凱家族的母親,畢業於北平輔大、師出著名史家陳垣,王光美是同學,劉鳳學是「閨蜜」,常來吃飯。
雖然二〇〇六開始對起透過「陳映真研究」我開始有了些理解,讀肥作算是在補課,沒法多說什麼,只能gossip認識的肥。此人跟那一代人一樣複雜,他更難纏,不容易疏理,硬著頭皮試試看,不要揍我就算完成任務。
初識肥是一九八五年在芝加哥,跟Penny、YY等從柏克萊去參加他推動的「台灣社會國際研討會」,吃了他牛肉麵,見到已故的mentor錢新祖(Edward)、阿偉(舒詩偉)老林/孝信、陳/美霞、李歐梵(Leo)、蔡仁堅等。後來在紐約教書,肥跑來要我寫東西評論「河殤」。完成學業後,肥去了香港浸會大,住過他的宿舍,認識Jolanta跟兒子,也認識一群朋友。
記憶最深的是「天安門民主大學」,他跟潘毅等一些學生,從廣場回港後整理了很多資料,他家裡還留著。期間,我們因ARENA偶爾相遇。浸會大學退休後,肥回台在中研院「復職」,每個月都會在台社見到。後來到苦勞網才知道他在那兒搞了一間辦公室,開始了龐大的寫作計畫。
肥的複雜性至少由幾種不同的資源與身分位置構成:
母親造就的家學淵源、音樂作曲/小天才、中措生、民歌採集者、原民情懷、皇親國戚、政治犯、小商人、人類學家、社運流浪狗(他自己的講法);其實「流浪」是構成肥一生的特性。年少時因家庭背景、接觸到不同的資源,可以任性的不鳥正規的社會常規,成為中措生,在台、師大晃蕩或謂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