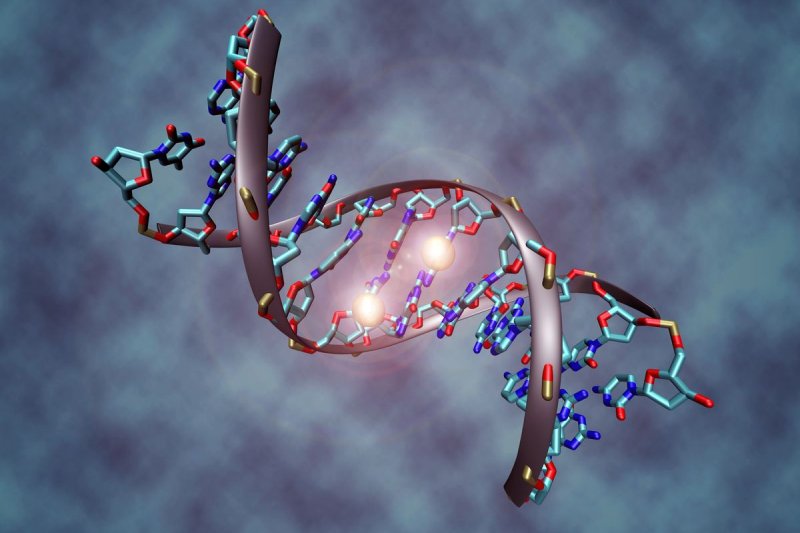在我的童年和成年生活中,莫尼、賈古和拉結什是家人心中莫大的陰影。青少年時期我有半年因為莫名的煩惱而不肯與父母說話,不交學校作業,還把舊書都扔進垃圾堆。父親心急如焚,拽著我去看當初診斷賈古的醫師。現在是不是輪到他的兒子也瘋了?祖母八十歲出頭時記憶衰退,開始誤稱我為拉結什瓦(也就是拉結什),起先她還會尷尬臉紅,自我糾正,但後來她不再理會現實,似乎情願錯認,彷彿在這樣的幻想裡自得其樂。在我認識如今成為我妻子的莎拉時,也把堂哥和兩位叔叔精神分裂的情況向她說明了四、五次,我想,面對未來的伴侶,應該發出這樣的警告才公平。
那時,遺傳、疾病、常態、家族和特性已經成了我家人經常談論的話題。就像大部分的孟加拉人,我的父母壓抑和克己的功力幾乎已臻化境,儘管如此,依舊難以避免這段家史問題。莫尼、拉結什與賈古:三段被不同精神疾病折磨的人生,很難讓人不去聯想這個家族背後隱藏著某個遺傳的問題。莫尼是不是遺傳了某個或某組基因才讓他罹患精神疾病?這是否與影響我兩位叔叔的基因相同?其他家人是不是也會受到其他精神疾病的影響?我父親就至少出現過兩次精神病的症狀──後來都是靠服用印度大麻(bhang,搗碎大麻芽,融進酥油,再攪拌起泡,這是一種宗教節慶的飲料)把症狀壓了下去。這些和我家族從前的創疤有沒有關係?
二〇〇九年,瑞典學者發表了規模龐大的國際研究,受訪者包括數千個家族、成千上萬名男女,研究分析了帶有跨世代心理疾病史的家族,最後有了驚人的發現,研究成果顯示躁鬱症和精神分裂有密切的基因關連。研究中,某些家族具有和我家極其相像的交叉病史:一名手足精神分裂,另一名躁鬱症,還有一名甥/姪(女)也精神分裂。二〇一二年,幾項進一步的研究更確認了初步發現,確定這些精神疾病的變異和家族史的關係,也更進一步探究其病因、流行病學、觸發因素和始作俑者。

由加爾各答返回美國後的某個冬日上午,我在紐約地鐵讀到兩篇這樣的研究。走道對面有個戴著灰色毛皮帽子的男人正壓制著兒子,也要為他戴上灰色毛皮帽。地鐵到了五十九街,一名母親推著雙胞胎嬰兒車進來,兩個嬰兒一同發出在我耳裡聽來一模一樣的尖叫。
這些研究給了我莫名的撫慰──回答了糾纏我父親和祖母多年的問題,但也激發了更多的新問題:如果莫尼的病是遺傳,那麼他的父親和姊妹為什麼能逃過一劫?觸發他們發病的是什麼?賈古和莫尼的病有多少比例源自「先天」(即容易發生精神病的基因),又有多少比例出自「後天」(如時局動盪、爭吵和創傷等環境的觸發因素)?我父親是否也帶有這樣的基因?我呢?要是我確知了這個遺傳缺陷的本質,我會怎麼做?我會不會為自己或為我的兩個女兒做測試?我會不會告訴她們結果?要是只有其中一個女兒帶有這樣的印記,又該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