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詩是現代詩人為安定自己的騷動靈魂而寫的,最精彩、最迷人的現代詩幾乎毫無例外,都有著強烈「為自己而寫」的動機,不同於傳統詩「為他人而寫」的出發點。
出於「為自己而寫」的安魂需求,現代詩理所當然運用了詩人的「私人語言」,他和自己的對話,他為了自己而或勇敢或膽怯或囂張或絕望地和外在世界對話,要能發揮這種給自己安定心魂、至少是找到一種發抒騷動不安心情的作用,他無法用普通的、一般的語言。
閱讀「真正的」現代詩,我們沒有理由、沒有必要、沒有資格去問:「為什麼你寫的詩我看不懂?」你看不懂,就表示你不是他的讀者,你身上沒有他的不安、他的焦慮,沒有他要自我克服的那份「現代艱難」。
現代詩人最難的,不是掌握一套固定的寫詩技法,不是贏來讀者、和讀者溝通,而是說服自己、和自己溝通。
讀現代詩,不是去感知詩人要跟我們說甚麼,而往往是驚異、意外地發現他所表現的,不管用怎樣的形式,直接撞進你的心中,釋放你自己壓抑的焦慮,或替你描述了、表達了你內在自己都不知該如何讓它成型的曖昧、隱晦情愫。
許多現代詩的共同作用,在於說服詩人自己:這個世界,不管如何瑣碎、無趣、危險、滑溜、醜陋、扭曲,仍然是值得忍耐的,值得繼續跟它周旋下去,仍然有機會找到一點安靜安穩。和詩人活在同樣的時代、類似的環境中,有著同樣的懷疑、類似的沮喪,我們讀到他們寫的詩,也就跟隨著被「安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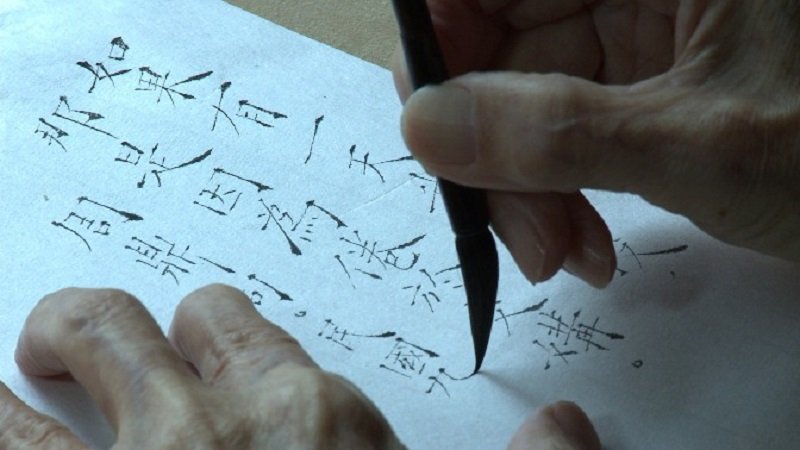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五年,「黃金十年」間寫現代詩的這些詩人,是台灣歷史上最不安、最焦慮的一群靈魂。他們成長在一個不知和平為何物、不知「正常生活」為何物的中國社會。先是抗日戰爭,接下來立刻爆發了國共內戰,戰爭不放過他們,緊追著他們,而且戰爭給他們帶來愈來愈深的困擾與痛苦。
前面,抵抗日本人,打日本人,至少還有一個比較簡單、比較清楚的立場;後面,變成了中國人打中國人,不再有那麼非打個你死我活的理由,偏偏還是進行了兩不相容的死活爭戰。
更慘的是,他們屬於打敗仗的那方,屬於「你死」而不是「我活」的那一邊。年紀輕輕地,他們就被死亡的陰影追趕著,離鄉背井逃到台灣來。台灣是從北而南、從西而東的逃亡路線上的最後一站。再往南,就只剩大海了;再往東,也就只剩大海。逃難逃到台灣,意謂著退無可退,意謂著規避毀滅的最後一個牆角。
這樣的生活,惶惶不可終日。不能向前想,因為不知道明天會怎樣,沒有未來;也不能向後看,因為那是徹底改變了,回不去的家鄉。可是他們又能有怎樣的現實呢?貧窮、艱困、挨餓、受凍、撤退、奔逃,還有,一個陌生、敵意的新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