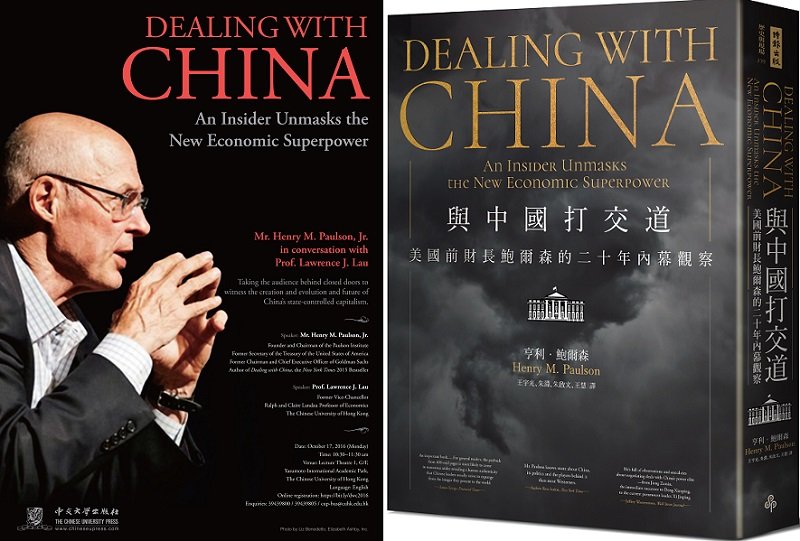「別叫醒總統,」哈德利說,「把羅伯.蓋茨叫醒就行了。」
我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認識了國防部長。我非常尊重他。但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通他的電話。我得先跟一幫軍銜很高的副官打交道,還有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一個副官以不屑的語氣問我,究竟為什麼打這個電話,我不得不拿架子了:「我是財政部長,」我說,「把蓋茨部長叫醒。」
我過去從來也沒有這樣拿架子,以勢壓人,以後也不會。
羅伯終於在電話那邊睡意朦朧地問,「這是怎麼回事啊,漢克?」
我直接告訴他,我在北京,美國海軍艦船不能穿越台灣海峽。
羅伯迅速按照我的期望做了,換了我,形勢發生逆轉,我也會這樣做。
「如果這對你很重要,漢克,我們取消這次行動。」
我在電話裡聽到有人在旁邊碎碎念──事實上,是極度的驚愕──我決定掛斷電話,別等到發生爭執,或者再出現變故。我只是說,「非常感謝,我看重這個決定。這很重要。」
我回到了SED會議,告訴桑迪:「解決了。軍艦改道了。」我得承認,我鼻子都氣歪了,但並不是因為過度自負而在海軍計劃問題上小題大做。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所有美方參加SED的人都知道,中方不會認為這樣的插曲是偶然事件。在一個很重視跡象和象徵性的文化裡,無論大小事,每一個行為和事件都被賦予了意義。缺少透明的封閉決策過程,更放大了這種趨勢。
回到華盛頓,我還有點不高興。但布希總統卻覺得我咄咄逼人的行為很有意思。回來後的一次內閣會議上,布希總統衝我咧著嘴笑出聲音。「為什麼你花那麼長時間才找到蓋茨?」他風趣地問,因為他知道我當時急切地要跟國防部長通話。總統有幽默感,喜歡頑強的人。在我們面臨嚴重金融危機時,這兩個性格特點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