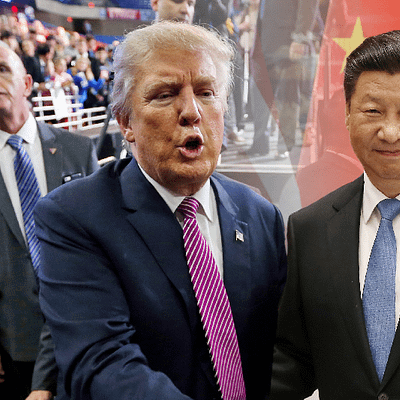自從農業發端,貨物與工具的遠距移動就一直是人類文明的特質。地中海貿易是雅典人、古迦太基人和羅馬發展的核心。穆罕默德是貿易商,而穆斯林世界的貿易路線,以及通往亞洲的絲路,維繫了西方整個中世紀的文明之光。
大量移民也是早期歷史的特質。許多大帝國建立,後來又被從北亞向南、向西、向東湧入的游牧部族所摧毀。日耳曼人、匈奴人、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其他族群,通常以暴力入侵已經建立的文明,以尋找、征服、最終安頓在更肥沃、開化程度更高的土地,直到下一波游牧民族的攻擊來襲。

十五世紀時,歐洲遠洋海權的興起,為這個時期畫下句點。在此之前,地球上大部分土地都為安土重遷的農業社會所占居。歐洲人探索海路與陸路,通往大半個世界,在他們視為弱勢或「次等」文明的地區殖民。隨著巡航技術進步,安定的母國之間在貿易、殖民地的掠奪也跟著擴展。貿易成為國家最重要的問題。
在十六與十七世紀期間,結合殖民主義與貿易的主要哲學是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者相信,統治者應該設法把貨物銷售至海外,同時進口愈少愈好,這樣才能累積資本,最好是累積強勢通貨。為了刺激財富累積,重商主義者支持由國家控制經濟,包括對出口品補助、對進口品徵稅。有些重商主義者,如《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的作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就主張無限制移入移民,希望移民能與本地勞工競爭,壓低工資。同理,他們對移出移民戒慎小心,因為這會減少全國勞動力的規模,從而減損生產出口品的產能。
重商主義反映了當時統治階層的利益。重商政策加重一般人的負擔,但是為國家累聚積蓄,供統治者運用,建立軍事優勢,維持公共秩序。在那些統治者眼中,人口是可以剝削的資源,而不是他們應該為之服務的公民。

在十九世紀期間,許多我們在前述章節討論過的激進派思想家,發展出貿易的新理論。邊沁、亞當.斯密和休謨把經濟分析的焦點從君主累積財富的利益,轉移到庶民享受繁榮的渴望。他們相信,各種經濟自由(跨國界交易、借貸、土地和其他資金的新用途和出售等等)是一國經濟能帶給其國民的總福利達致最大化的關鍵要件。由於著眼於市場利益,他們擁護自由的國際貿易,反對獨占與國家對國內市場強加的限制,如價格控制。當時的激進市場是跨越國界的市場。
在移民還不重要之時
雖然早期激進派人士熱情地擁護自由貿易,他們對於移民的論述卻甚少。這點或許看似奇怪:自由移民與自由貿易的邏輯源出一理,也就是經濟開放的延伸,能為幾乎所有人帶來財富。順道一提,這些思想家當中也有部分人提到,不只是貨物,他們支持人民的自由移動。例如,亞當.斯密與李嘉圖都曾主張勞工可以從鄉村自由移動到城市,也可以自由轉換行業,並順理成章地論及,跨國界的移動也適用於同樣的道理。他們也強調思想自由流通的重要。不過,在他們的思想裡,自由貿易一面倒地壓過自由遷移。

對貿易的強調勝於對移民的強調,一個原因是在十八與十九世紀,自貿易而來的利得,遠比自移民而來的利得重要。原因在於,儘管各國歷經繁盛與衰退的時期各有起落,公眾生活水準在各國間持續的差異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都不為人知。即使最極端的差距,例如中國與英國之間,也只有三倍,這與1950年代出現的十倍鴻溝,有如小巫見大巫。
要衡量貧富差距,一個理所當然的方法就是計算個人平均所得在平均分配之後所能增加的幅度。例如,假設現在有兩個人,其中一人的所得是100萬美元,另一人是1千美元。如果我們均等分配所得,第一個人的所得會下降到50萬500美元,也就是跌幅將近50%。第二個人的所得會增加到50萬500美元,增幅為五百倍,也就是50,000%。因此,所得均等化會造成所得平均增幅大幅增加,略低於24,975%。8對比之下,在一個人人所得相等的社會,用這種不平等衡量指標所計算的結果會是0。數字愈高,社會愈不平等。
*作者格倫・韋爾(Glen Weyl),微軟研究院首席研究員,耶魯大學法學院與經濟學系資深訪問研究學者。艾瑞克・波斯納(Eric Posner)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與美國法律協會會員。本文選自兩人合著之《激進市場:戰勝不平等、經濟停滯與政治動盪的全新市場設計》(八旗文化)。本系列結束。 (相關報導: 全球化面臨考驗,新冠肺炎疫情過後的新世界更趨數位化 | 更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