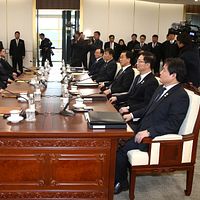去年,文白之爭又起,熱鬧過後,問題依舊。文白之爭,彼此意見迥異,看似爭鋒相對,實則兩方各為爭持而引喤,自唱抒懷,並無交鋒。既乏互相詰問駁難,自無「真理愈辯愈明」。從而擬由雙方歧議中,折中出精華,好理曉文言和白話的錯綜關係,進而融會貫通國語文學習之道,戛戛乎而莫得焉。更糟的是,雙方所展現的論述姿態,均難脫「不講理」嫌疑。
文白之爭,一世紀以來,從未消停。有道是:「語言的問題從來不曾是單純的語言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文化的問題茲事體大,而且牽涉個人對於文化的情感認同與價值取捨,易鬧意氣。回顧一世紀以來的相關爭論,便時見意氣之爭,竟而演變成無謂之爭。感嘆萬端,是歷史不能給人教訓,還是有人不願受教訓?文白爭論諸般現象,值得了解;其中的教訓意義,應當謹記。
西元1917年元月,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雜誌,登出26歲青年胡適寫的〈文學改良芻議〉。雖然標題「溫和而謙虛」,實則意在張揚文學革命旗幟,強調「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接著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公然宣示「高張『文學革命』大旗」,聲援胡適。也正式發動中國現代史上,轟轟烈烈的白話文運動。
白話文推廣在1919年五四運動後,如胡適說的,「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文成為全國通用書面語。而原先盤根錯結,根深葉茂的文言文,兩千多年來,一直是最主要的文化傳承媒材。如今面對白話文的挑戰,竟似摧枯拉朽般,毫無招架之力。當時一心捍衛古文的林紓,只能不甘心說:「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早有人提倡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1898年《無錫白話報》創刊,主編裘廷梁就呼籲「崇白話而廢文言」。他說:「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見解相若者,不乏其人。用言論提倡白話文外,有人辦起白話報刊。自1897年至五四前夕,中國各地刊行過的白話報刊,多達一百七十餘種,猗歟盛哉!
白話報刊紛起,卻未能使白話文推行開來。原因多樣,本文無法細究,僅就語文層面相關的一點來說。那些白話報刊,許多其實是方言報,流行範圍受侷限。使用方言能達到言文合一效果,看似方便,卻未能顧及書面語有規範口語的作用。加上近代新文明不斷有新概念生成,衍生新詞語,書面語應具備什麼條件方能順應時代之變,時人缺乏了解。
白話文運動以古白話為基礎,融匯文言、口語、方言中有生命的語言。既能靈活書寫表達意思,又具開放性,能吸納層出不窮的新詞語。同時間還有國語運動在進行,其旨在規範及確立國民共同標準語。兩運動相配合,相輔相成。胡適就鼓吹「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強調「若要活文學,必須用國語」。至今仍有許多人不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而已,還以為文白之間,說切割就切割。或者以本土立場,刻意抬舉方言地位。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以文白之爭遂行政治目的,犧牲的是教育 | 更多文章 )
白話文不特證明是創作新文學的利器,更是傳播新思想的有力媒介,給老大的中國帶來文化新氣象。白話文運動屬新文化運動一層,新文化運動過程中,卻不時出現和其所宣傳的理念相牴觸的現象。例如,胡適信奉實驗主義,實驗主義反對教條,認為真理「不過是人造的假設」,主張「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對於提倡白話文,胡適表示,態度「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陳獨秀的態度則不然,他認為「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