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俄羅斯軍隊從布查鎮撤退後,當地居民開展一場大規模的行動,尋找死者屍體並查錄身份。這是一項非常嚴峻的任務。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也加入了當地警察和死者家屬的行列,並親眼目睹這一悲慘景象。
警告:本文包含可能讓人感到不安的圖像。
警察局長洛巴斯(Vitaliy Lobas)坐在布查鎮一所廢棄學校的兒童課桌前,收集死者屍體的詳細信息。
洛巴斯的肩膀很寬,一頭黑髮,說話非常簡練。每隔幾分鐘,他的手機就會接到一通電話,簡短的對話都是一樣的內容:死者屍體的位置,一些具體細節,死者親戚或朋友的電話號碼。

在俄羅斯軍隊佔領布查鎮之前,洛巴斯在當地擔任警察局長,主管布尚克西一區(Buchanksy District 1)。戰爭爆發前,他每天都在處理當地的普通犯罪案件和偶爾發生的謀殺案。自從布查鎮收復以來,他的每一天就是在這個廢棄的學校教室裏度過的,四周牆上還掛著一些裝飾畫。他在這裏負責指揮協調當地尋找死者遺體的大規模行動。
在洛巴斯面前的課桌上擺放著一張布查鎮的地圖。這座位於基輔郊區的一座籍籍無名的寧靜小城,現在卻變成一個巨大的犯罪現場。俄軍在向烏克蘭首都基輔發動進攻,並佔領了這座小鎮長達一個月。布查鎮最近被收復後,開始調查大屠殺慘案。這是一個緩慢而痛苦的過程。
每次電話響起,洛巴斯都會查看擺放在面前的地圖,然後在一張紙上,一行接一行地寫下必要的信息,字跡很工整。 到中午時分,他已經填滿了一張16開紙,然後開始寫反面。 他說,前天找到64具屍體。大前天,找到37具屍體。他不知道這一天能找到多少受害者遺體,但他預計這個數字會增加到40人左右,因為人們在附近正在挖掘一個亂葬坑。洛巴斯只負責這片區域,在他的管轄範圍之外,人們還發現了更多的屍體。

洛巴斯偶爾會停下來,抽空走到學校操場上抽支煙,但即使是休息片刻,也被電話打斷,有人向他報告發現的屍體或者詢問與收集屍體有關的問題。布查鎮正在下雨,一輛向太平間運送屍體的箱形貨車被困在泥裏,需要盡快找到拖拉機解難,因為眼下這種箱型貨車數量有限,遺體的數量卻不斷增加。洛巴斯通常將處理屍體現場的工作交給他的副手,但在接到案情嚴重的報告時,他會親自去現場處理。
「例如,當受害者雙手被反綁在背後,頭部遭到槍擊,我會親自去,」他說。
「如果屍體遭到焚燒,我也會去」。
大約上午時分,洛巴斯的一名24歲副手庫什尼爾(Dmytro Kushnir)打來電話,要求登記一具屍體,據報屍體位於布查鎮郊區的一棟公寓樓後面。
這座建築獨自矗立在林地邊緣的一片未開發的綠地上。當庫什尼爾到達這座建築時,他在公寓樓後面與樹林相交的地方發現了兩具男屍。 現場有兩名男子戴著藍色的手術手套,俯身查看其中一具部分腐爛的屍體,死者似乎是後腦勺遭到槍擊。屍體躺在一牀印有紅花的白色羽絨被上,被子很髒,旁邊散落著一些空啤酒和烈酒瓶子。這兩名男子戴著藍色手術手套,最初給人印象以為他們是醫療官員,但他們自我介紹說是沃拉迪米爾(Volodymyr)和謝爾希·勃列日涅夫(Serhiy Brezhnev),是死者的父親和哥哥。躺在羽絨被上的死者是30歲的廚師維塔利·勃列日涅夫(Vitaliy Brezhnev)。在俄軍佔領布查鎮之前,他和女友就住在旁邊公寓樓的六樓,過著平靜的生活。


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在一個月前與維塔利失去聯繫。當時俄軍佔領了布查鎮,通訊完全中斷。由於無法進入郊區去查看維塔利住的公寓樓,他們就在網路上搜尋了一個月,也設法在社交媒體上找到他還活著的證據,但是一無所獲。
俄軍最終撤退了。一個多星期前,哥哥接到弟弟女友的電話,講述了弟弟的遭遇。 她說,俄軍士兵襲擊了公寓樓,一路用霰彈槍射擊,轟開所有的公寓門,要求居民交出他們的手機芯卡和鑰匙。她說,俄軍士兵將她和弟弟關在不同的房間進行審問,毆打他們,並射殺了他們的愛犬。然後這群士兵把他們和其他居民押送到地下室,鎖住了大門,但是卻把弟弟單獨帶走,並告訴她再也別想見到男友。確實,她此後再也沒有見到他。
烏克蘭軍方宣告,布查鎮已經恢復安全,居民可以返回;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就出發前往這座公寓樓。走進大樓時,他們發現樓梯間的地板上沾滿血跡,周圍散落著居民們的個人照片。在每一扇單元門上,你都可以看到霰彈槍轟擊的彈洞——有時一個,有時四個或五個。有的鋼製安全門還被撬開了。 在一扇木門上,門鎖遭到多次槍擊,仍然打不開。可以想象,俄軍士兵變得非常沮喪,乾脆把門中間炸開一個大洞進入公寓。在另一扇公寓門後面,很明顯房主將一張沉重的桌子頂住門框,試圖阻止俄軍進入,但未能成功。

父子二人爬到6樓時,發現83號公寓的門已經被霰彈槍轟開。單元裏散發出一股刺鼻的氣味。哥哥猜想,俄軍士兵把公寓翻弄得一片狼藉,甚至還撬開了通風口和浴室的排水管,很可能是想找到隱藏的現金。哥哥希望發現弟弟還活著,但是他受到一次又一次打擊。當他進入弟弟的臥室時,枕頭上有很深的血跡,血濺到牀頭後面的牆壁上。地板上亂扔的雜物中有兩個7.62毫米的子彈殼——這是俄羅斯軍隊普遍使用的步槍口徑。
「你可以看到有一個人在這裏被殺害,」謝爾希說。 「但是沒有屍體」。
於是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開始尋找維塔利,他們心裏明白現在尋找的很可能是一具屍體,而不是可以再次擁抱的兒子和弟弟。謝爾希隨身帶著一張弟弟的護照照片。 「我們找了又找,」他說。「起初我們在尋找他的面孔」。
警告:讀者可能感覺一下照片讓人不安


在這座公寓樓後院緊靠著樹林地方,人們發現了一個看上去很淺的墳墓,就開始挖掘。挖掘遺體需要時間。首先,他們看到了一牀他們不認識的有花卉圖案的羽絨被,仍懷著一絲希望。但當他們把屍體抬上來時,看到羽絨被裏面有一幅來自維塔利公寓的窗簾,然後看到死者的鞋子——他們認出了那雙鞋。此刻日光已經開始暗淡,他們必須在宵禁前趕回家,所以就用牀單蓋住屍體,但仍抱著一線希望。
「今天是最後一次接觸,」謝爾希轉天低頭看著屍體說道。「今天我們脫掉了他的鞋子,看到他的腳」。
因為維塔利的腳一直穿著襪子和鞋子,所以在地下埋了一個月後,他的腳比他身體的其他部分保存得完好一些。
「我們看到了他腳的形狀,」父親沃拉迪米爾說。
「然後我們仔細查看了他的鼻子和手的形狀,」謝爾希說。 「我們立刻就認出這是我們的血肉」。


父親沃拉迪米爾兩年前在布查鎮購買了這套小公寓——這是他對兒子未來的投資。維塔利一直在首都基輔的一家餐館當廚師,但是新冠疫情爆發後被解僱。隨後,他在建築工地上找到一些活,不過他希望能找到一個更穩定的工作。他深愛女朋友和家犬,而且在一個不錯的社區裏還有一套公寓。他生前喜歡釣魚、打獵,業餘時間還喜歡採蘑菇,烹調。
「弟弟在這裏過著平靜的生活,」謝爾希說。 「他是一個普通人,僅此而已,一個善良的人,但他付出了一切」。
「他是一個兒子,一個兄弟,」父親沃拉迪米爾說,強忍眼淚。
在公寓樓的前面,庫什尼爾警官正在填寫他的案情報告。沃拉迪米爾走到他的車前,拿了兩小塊硬紙板,在上面寫上了他的名字和電話號碼,還有兒子的名字和地址。然後他向鄰居要了一些透明膠帶來蓋住墨水字跡,因為布查鎮開始下雨。父親走回到兒子的遺體旁,這次他沒有戴膠皮手套。他親手將一張卡片綁在兒子的腳踝上,將另一張卡片綁在兒子的手腕上。
他說:「我不想失去兒子」。
庫什尼爾警官完成了的報告。洛巴斯局長安排專用汽車來運走維塔利的遺體。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一邊躲雨,一邊等待汽車的到來。
隨著時間的推移,警察局長洛巴斯在學校教室裏臨時建立的指揮所變得越來越忙碌。警察進進出出,不斷提交犯罪現場報告。洛巴斯辦公桌上的名單越來越長,他的電話一直響個不停。
路邊有一排被摧毀的俄軍坦克,人們在旁邊的一口井裏發現了一具女屍。在一棟公寓樓的九樓,也發現一具屍體。一輛運屍車的司機打電話說找不到被派去收集的屍體。一位女士走進教室親自報告她的鄰居已經死了。「我都知道了,」洛巴斯告訴她,希望她別打斷手上的工作。 「我們今天會盡量安排把遺體運走」。
這時,洛巴斯的父親打來電話。 「老爸,我實在太忙了,」他說。 「我一切都好」。
布查鎮警察局的兩個街區在俄軍攻擊中被摧毀,警察局長洛巴斯因為缺乏人力物力而苦苦掙扎。眼下,裹屍袋已經所剩無幾。在過去的幾天裏,他的團隊也在縮小,只剩下一些能夠承受這項新工作壓力的人。「那些脆弱的人一開始就跑了,」他說。 這項任務規模巨大,幾乎沒有給人留下任何情感的空間。
洛巴斯接到了另一個電話——發現9具屍體。他問:「在哪裏?」
電話來自鄰近警局。他們發現9具屍體被埋在附近的一片田地裏。洛巴斯掛斷電話,又撥通了他手下的一個機動小組。「那裏的團隊已經筋疲力盡,他們已經沒有裹屍袋了,」他說。 「他們一整天都在收集死者屍體,你們現在就去幫幫他們,帶一些裹屍袋,幫他們收拾遺體」。

在土路盡頭的波紋柵欄後面,這9座墳墓整齊排成一條線。俄軍佔領期間,鄰居們將死者的屍體埋在這裏,現在鄰居們在警察的幫助下將遺體挖掘出來。
「這些死者中有些人因為得不到醫藥而死亡,有些人是被俄軍殺害的,」來自農田旁邊一棟公寓樓的45歲烏克蘭人根納迪(Gennadiy)說。他當時幫助掩埋了這些死者,現在又是主要依靠他把遺體挖出來。
「他們都是我們的鄰居,」根納迪說,臉上流露出深深的憤怒情緒。 「這是隔壁公寓樓的托利亞叔叔( Uncle Tolya )和他的鄰居。這是我在隔壁樓認識的另一個人。這個死者有槍傷,我們不認識他,但我們在他的身上找到了護照。這個老太太患有嚴重的糖尿病,我們試圖將她送出布查鎮,但沒有人道綠色走廊,所以她死了。這名男子帶著他的狗出去散步,沒有回來。我們不是病理學家,不過他可能是被槍殺的」。


移走死者屍體的工作很艱巨。遺體埋的很深。雨水浸透了泥土,踩上去很滑。根納迪穿著綠色的塑料雨披,爬進每個墳墓,從死者屍體周圍鏟走泥土,這樣就可以在屍體周圍繋上粗帶子,把他們吊出來。
每具屍體都被各種手頭能找到的材料包裹起來——窗簾、不同顏色和圖案的毯子。警方對遺體進行了檢查,並用手機拍攝了遺體上任何明顯的傷痕。現在已經找到足夠的裹屍袋,過了一會兒汽車就到了。汽車後門覆蓋著泥巴,有人在上面潦草地寫著"200"的字樣——這是運送死者遺體的軍用標識。遺體都裝進了車廂。天空一片灰濛濛,雨一直在下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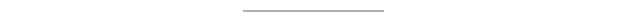
在維塔利所住的公寓樓裏,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一直在等待運屍車的到來。天色漸暗,他們需要回家。維塔利的屍體將不得不在外面再過一夜。 他們現在無法在晚上9點宵禁之前趕回首都基輔,不過他們在路上經過軍事檢查站時,出示了死亡報告後,執勤人員就揮手讓他們通過。
第二天太陽剛露頭,父子二人趕緊起牀,開車返回布查鎮。他們實在不能再等待運屍車了,於是將維塔利的遺體安放在車後座,開車向南跑了約一小時,終於抵達博亞爾卡鎮( Boyarka)的太平間。
在俄軍入侵之前,博亞爾卡太平間的工作人員習慣於每天處理大約3具屍體,其中絶大多數死於自然原因。39歲的彼得羅維奇 (Semen Petrovych) 說,自從布查鎮被收復以來,他們每天要對大約50具屍體進行屍檢,其中80%是死於暴力。他在那裏擔任法醫專家已經16年了。

太平間位於博亞爾卡鎮邊緣一家醫院後院建築內,周圍是一片森林。他們剛剛租了兩輛冷藏車,現在都裝滿了屍體。從卡車旁邊的地板到圍欄邊以及太平間入口的兩側都擺放著裹屍袋。
「我們沒有足夠的工作人員,也沒有足夠空間,」法醫專家彼得羅維奇說。 「即使我們有更多人手,又在哪裏存放屍體呢?」
通常,他會對每具屍體進行認真的屍檢,並打印死亡證明。 「現在我們只能快速驗屍,用手寫記錄,」他說。
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父子二人並不是唯一一個運送屍體的人。一些私家車開進來,停在太平間門前,把裹在毯子和地毯裏的屍體搬下來。還有一些死者的親戚和朋友來這裏尋找屍體。日連科女士(Tatiana Zhylenko)正在尋找一位朋友父親的遺體,這位朋友目前在國外。 「他胸前有護照,」她告訴工作人員。扎科沃羅尼(Oleksander Zakovorotnyi)是來尋找岳父的遺體。隆冬時節,俄羅斯軍隊切斷了天然氣供應,他岳父用天然氣罐組裝一個土製取暖器,但在火焰熄滅時睡著了,不幸煤氣中毒死亡。

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父子二人在外面等著,直到他們被叫進來確認維塔利的身份。他們站在狹窄、天花板很低的太平間裏,地板上和每張輪牀上都擺放著屍體,氣味很難聞。他們不得不擠在兩個輪牀之間,才能靠近維塔利的屍體,旁邊擺放著被解剖的屍體。他們在維塔利的遺體上尋找他們熟悉的傷疤。他們向病理學家反覆解釋,他們已經認出了維塔利的腳。父親將視線移開,又回頭看了看。他仍在懷疑和希望中掙扎著。
隨後,他走到冷藏車後面,獨自站著抽泣,淚流滿面,渾身顫抖。維塔利的遺體被抬出來,他的裹屍袋上標有552號——這是這個小太平間自年初以來處理的第552具屍體,幾乎是正常年份的兩倍,而且一周之內就增加了幾百具屍體。
警察提取了弟弟的指紋,並告訴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由於屍體積壓嚴重,正式鑒定需要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否則他們可以很快將弟弟的遺體送往墓地安葬。


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父子二人沒有等待專用運屍車,而是小心翼翼地再次將維塔利的遺體抬到他們的車後座上,開車一個小時左右回到布查鎮。一路上經過一排排被炸毀的房屋和設施,當時有許多死者的屍體橫躺在街上長達幾個星期。眼下,公墓內的墓地已經用完。鑒於此,沿著公墓邊界圍欄,緊靠公路,有一條狹窄的地塊。人們開始在那裏挖掘新的墓地。一位神父站在棺材前主持葬禮儀式,念悼詞並為死者祈禱。死者的母親嚎啕大哭。不遠處,在森林的那一邊,一顆未爆的炸彈被引爆,發出巨大的爆炸聲。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開車進了墓地,在一長排的裹屍袋旁邊將維塔利的遺體從車上搬下來。
因為維塔利已經被確認身份,將被安葬在布查鎮,所以他被安放在一個有棕色布內襯的簡易木製棺材中,並獲得了一點點尊嚴,可以暫時在墓地磚砌建築內安息。他將在兩天後安葬。
父子二人離開了墓地時,沃拉迪米爾決定,即使這裏距離他們在基輔的家很遠,他堅持要為妻子莉莉(Lily) 買一塊墓地。她是維塔利的母親,患有晚期癌症。當她離世時,會距離兒子近一些。
兩天後,在布查鎮一個寒冷的早晨,天氣晴朗,一家人聚集在墓地。沃拉迪米爾和謝爾希再次帶頭,走進磚房內,凖備抬棺材。莉莉獨自一人坐在外面的長凳上,抽著煙,周圍都是裹屍袋。兒子的棺材被抬到一個石頭台子上,全家人圍著棺材站成一圈,由神父主持葬禮,教堂的兩名老年婦女拿著香爐唱歌。隨後,一輛標有200字樣箱型汽車將維塔利送到公墓門外,在路邊的一處新墓地安葬。沃拉迪米爾仍在與懷疑作鬥爭。
「我仍然希望指紋能夠顯示這不是我的兒子,」他說。


那天晚些時候,警察局長洛巴斯已經回到布查鎮被廢棄的學校,正坐在課桌旁,仔細聽一個人親自來尋求幫助,他聽說他的親戚被埋在亂葬坑裏。 洛巴斯說,這名男子曾去過教堂旁的大型亂葬坑,但那裏的工作人員讓他來找警察詢問。他想給洛巴斯一張照片,但洛巴斯解釋說程序不是這樣的。 「我們不能拿著這張照片,去打開所有裹屍袋,」他說。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那樣做會浪費太多時間」。
洛巴斯解釋說,必須開始掩埋身份不明的死者屍體,因為太平間已經沒有存放的空間。不過,他保證,警方會採集死者的指紋並給死者拍照,這些資料都會保存下來。 「即使遺體被掩埋,死者的信息仍然會保留,」他說。 「死者的照片還在」。
電話仍然響個不停——在亞布倫斯卡街(Yablunska Street)發現了一具屍體,在一所學校旁邊找到另一具屍體。「我們已經排查過這兩個地址,新的發現給我們增加了工作量,」洛巴斯說。 他現在稍加休息,可以到學校操場上抽支煙。他說,現在每天收集的屍體數量開始下降。 他認為這項工作可能很快就會結束。「現在這裏沒有周末,我們將繼續工作,直到收集完所有的屍體,他說」。
他把煙頭一扔。電話又響起來了……
Rita Burkovska參與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