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有《保守主義的意義》、《政治思想辭典》等經典的當代思想家羅傑.斯克魯頓(Sir Roger Vernon Scruton)1月12日在英國病逝,享壽75歲,距離他被診斷出癌症僅僅6個月。斯克魯頓一生致力於探究使西方文明得以偉大而獨特的原因,並冒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為其辯護,因而時常招致意見不同者批評,甚至是抹黑。
去年斯克魯頓接受《The New Stateman》專訪,記者斷章取義的報導使他丟了政府的差事(保守黨執政下美化建築的委員會Building Better, Building Beautiful諮詢委員)。雖然事後《The New Statesman》為錯誤報導刊登了道歉啟事,斯克魯頓也重回委員會,但當時報導一出,英國輿論對斯克魯頓未明究理便群起而攻之,包括多位保守黨議員與倫敦《標準晚報》總編輯、曾任英國財政大臣的奧斯本(George Osborne)都對斯克魯頓開砲。
此事在以自由為傲的英國歷史中,留下了黑暗的一頁,也反映了斯克魯頓的思想自始至終總是充滿爭議,卻鮮有人願意細探他的思想內涵。
傳統的文人之風
斯克魯頓的思想深植於英國的文化傳統。稱斯克魯頓為思想家似乎稍嫌籠統,不過因為他屬於「上一個時代」,有過往文人那種文史哲不分家的遺風,所以硬要為他在文化上的貢獻歸類,反而顯得狹隘。斯克魯頓一生出版的書籍約有50種,可謂著作等身,討論的議題包括美學、文學、建築、政治、哲學、性別問題、國際關係、動物權、環保、宗教等等。
除了涉獵範圍包羅萬象,創作的範疇更彰顯斯克魯頓是一位萬事通。在學術的專著與報刊雜誌的評論之外,短篇故事、長篇小說、柏拉圖式的對話錄都難不倒他,遑論他還學過作曲、寫了兩齣歌劇。斯克魯頓為《泰晤士報》等報章撰寫的專欄,主題更包括音樂、狩獵、紅酒與摩托車維修,他也因為在專欄中批評民權運動與反越戰運動飽受左派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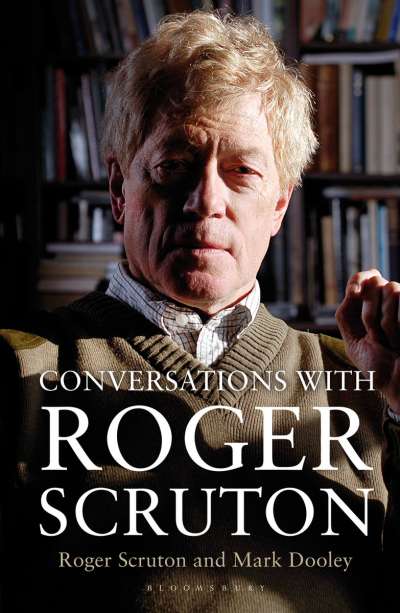
在一篇自傳式的書評中,斯克魯頓回憶道當年就讀文法學校的青少年時期,一心向學的其實是科學。但是他很快便發覺科學無法完全滿足他的求知欲以及對人生的困惑,所以便開始廣泛閱讀人文書籍。起初他很崇拜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但在劍橋大學接受了分析哲學訓練後,斯克魯頓卻發現過往心儀的歷史哲學缺乏邏輯論證。
然而,一味以科學的方法與內容為宗的當代哲學,對他而言依舊是匱乏的。斯克魯頓追求的是一種文化視野,其觀察對象與科學視野所關心的是同一個世界,但是所見之處皆是人文價值而非物體的碰撞或力的作用。他認為,即使斯賓格勒的哲學有諸多缺陷,在融哲學、歷史與藝術之洞見於一爐、並彰顯人文的價值之下,這樣的哲學滿足了當時西方文化最深遠的渴求。這也是當代哲學應做卻力有未逮之處,於是斯克魯頓便將人文價值的探究與捍衛視為他畢生的工作。
在英國的文化傳統中,這並不是甚麼劃時代的創舉,在斯克魯頓之前,也有許多文人以對抗科學對人文價值的侵害為志業: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阿諾德(Matthew Arnold)、拉斯金(John Ruskin)、T. S.艾略特(T. S. Eliot)、卻斯特頓(G. K. Chesterton)、C.S.路易斯(C. S. Lewis)以及利維斯(F. R. Leavis)。
斯克魯頓的獨到之處,在於他得惠於分析哲學的精準語言,將科學與文化的分野清楚地定位在不同的理解模式,而非人文學科所處理的現象不屬於科學能觀察到的範圍。這使他在晚期有名的《Gifford Lectures The Face of God》中得以說明,我們如何能在接受現代科學對這個世界的描述之下,同時相信基督教的教義而不致落入迷信;為什麼科學家只看得到自然世界,而我們因為身為人所以在同一個世界中能看見上帝的臉,就如同我們在畫中看見的不是粒子,而是蒙娜麗莎。
邁向公共知識分子之路
斯克魯頓擅長於將其他哲學傳統乃至於其他學科中的洞見,以分析哲學的語言清楚表達出來。例如他的美學博士論文雖然奠基於維根斯坦的理論,卻不吝於引進歐陸現象學在這個領域內的重要發展。可是這也同時表示,如果他能悠遊於各種寫作手法,當時代浮現相關需求,他也不會永遠被侷限在分析哲學的學術殿堂中。

1978年,斯克魯頓受保守主義歷史大家考林(Maurice Cowling)的邀請,加入了索茲伯里小組(The Salisbury Group),並發表了〈The Politics of Culture〉一文,奠定了其日後政治思想以「人格」為核心概念的發展路線。
1970年代是與保守黨有密切關聯的各大智庫興起的時代,著名的柴契爾夫人與基思・約瑟夫爵士(Sir Keith Joseph)所創辦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便創立於愛德華・希思(Edward Heath)所帶領的保守黨輸掉大選下台的1974年,以政策為導向、受經濟自由主義影響頗深的亞當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則成立於1977年。
斯克魯頓與許多保守主義學者如歐克秀(Michael Oakeshott)、肯尼思・米諾格(Kenneth Minogue)等人參與的保守哲學小組(The Conservative Philosophy Group)也在同一時期成立,這個小組想為保守黨重掌政權創造理論基礎,柴契爾夫人在擔任首相前,也曾參與他們的活動。不過斯克魯頓較少觸及經濟議題,他更常處理的是道德、文化、社會、政治議題的保守觀點。
雖然從政治史來看,這些智庫對保守黨的政策影響有限,但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1982至2000年斯克魯頓主編的《索茲伯里評論》(The Salisbury Review)雜誌確實意義重大。這本刊物為保守派的政治立場提供思想彈藥,經常批評核裁軍運動、女權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斯克魯頓在《新左派思想家》(Thinkers of the New Left)一書中,則把當時如日中天的沙特(Jean-Paul Sartre)、傅柯(Michel Foucault)都當成論敵。
左打社會主義、右打自由主義
斯克魯頓對1980年代保守主義的思想主要著力點有二。首先,要處理那些自由主義無法處理或不願面對的問題,而這些問題的話語權卻一直掌握在左派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手中;其次,提出論述時必須挑戰固有的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概念,並以保守的概念替換之。這種論述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保守主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Conservatism)一書中對人在現代社會感到疏離的討論。
這個問題向來是資本主義被左派攻擊的死穴,其中馬克斯主義認為人會感到疏離最主要的原因是私有財產制,在市場的自由交換中,工人階級所付出的勞動被剝削,他們既得不到其應有的工資報酬,工作的內容也無法賦予生命意義。
斯克魯頓同意現代社會有此問題,也同意自由主義於事無補,但不認為問題的根本出在財產制度。他借用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的論證,說明為何財產是人在這個世界上獲得歸屬感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並反過來指出現代社會使人感到疏離最重要的原因,出在另外兩大意識型態對這些使人的生命能夠獲得意義的制度與組織不夠重視。
自由主義太過重視「自由」,忽略了在英國所謂自由指的是能去做任何法律沒有禁止之情事的自由。但法律所禁止的東西,反映的是一個社會在過去數百年逐漸達成的共識,沒有了這些人們應如何一起和平生活的共識,現代人所擁有的自由便難以蘊含除了滿足個人慾望之外更高層的意義。社會主義則太過強調「平等」,忘了不平等是自由結社的必然結果,如果因為追求平等反倒壓抑了社會上的各種交流與活動,則離共產世界亦不遠矣。
反共:民主與人權之外
強調結社自由與生命意義之關聯的論點,在冷戰的歷史背景下,代表的是對共產主義的缺陷更深入的分析,同時也點出西方的政治文化裡真正有價值的部分在哪裡。在東歐與蘇聯共產政權於1989年垮台之前,除了在經濟與軍事上與之抗衡對英國來說特別重要,更為關鍵的是在思想上的對抗。對斯克魯頓而言,標舉民主與人權是無用的陳腔濫調。英國在民主化、擴大投票權之前,早已享有各式各樣的自由,並締造了輝煌的帝國主義,四處傳播自由的生活方式;而雖然一直缺乏一部成文的人權法案,在英國的生活中人民所享有的權利卻可能是世界上最多樣而豐富的。
斯克魯頓因此提出了人格的概念,並用此說明共產與自由之差異主要在於結社的傳統。他認為各式各樣的組織乃至於國家本身,不僅有法律上的人格,更具有道德意義上的人格。就像面對一個人行為我們會下道德判斷,對社會上的機構以及國家的行為我們也同樣會表達讚揚或貶抑。但是人格無法獨自享有,需透過人與人之間的理性互動中相互承認,才有可能實現。
在英國法律的傳統下,成立一個社會機構不需要經過國家的認可,也沒有文件需要申請、簽署、蓋章,只要公開成立,法院便會為其享有的權利捍衛到底。這個傳統展現的正是國家透過尊重社會機構的人格而實現其自己的人格。所以我們要防範的,不是國家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是當國家喪失人格變成機器,從而泯滅包括你我個人以及種種社會組織的人格。共產的社會裡,所有的社會機構都成為國家控管、領導的機器,成為追求某一特定共同目標的工具,就是國家喪失人格的後果。
斯克魯頓由此立場出發,捍衛了許多招致爭議的主張。例如大學這個機構本為學者們為追求研究結社而生,若國家以追求資源分配之平等為由,強制要求其招生不能只以學術能力為標準,而應為特定族群加分或保留名額,便是戕害大學人格的舉措。又例如死刑制度的存在說明的是有些罪行之重大只有最嚴厲的刑罰得以反映,若將刑罰理解為預防犯罪或是改造罪犯的工具,等同於將國家變成操控統計數字的機器,如果一個國家無法對破壞社會秩序的人表達意志,在戰爭中他又如何能教那些保衛社會的人去為國家、為一個機器而死?最後,車諾比事件發生之時,斯克魯頓也一再強調,問題不在於核能本身安全與否,而在於國家變成機器之後就只須對自己隨意訂立的發展目標負責,而不必在乎人民、土地與環境。
政治不正確的代價
篇幅所限,斯克魯頓在其他政治議題如脫歐的貢獻,在此只能略過不談。但斯克魯頓不只是一位思想家,而是身體力行的實踐者。他曾長年在東歐參與地下學術活動、引介禁書,協助被共產政權迫害的知識分子,因此甚至曾遭驅逐出境。反共也毀了他的學術生涯,申請升等時,因為曾在報刊發表過政治不正確的言論,而不是因為美學專業研究的不足,而被駁回。他主編的雜誌更因為出版社被左派知識分子恐嚇,而易手出版,更別提在該刊物發表過的作者時常面臨被炒魷魚的威脅。
斯克魯頓辭世,是英國的損失。英國能有這樣的損失,是身在台灣的我們羨慕的事情,因為我們的政治辯論,還停留在只反對共產黨表面上令人厭惡的部分。因為不了解共產黨,所以我們沒有察覺到,我們所追求的政治目標,某方面正使我們越來越像共產黨。
斯克魯頓遺孀一位,遺子兩名,據他的個人網站新聞稿所述,他全家人以他為榮,以他終身的成就為傲。
作者:崔麐,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政府與國際事務學院博士生,由政治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保守主義的流派與變遷。譯有《思考:哲學裡的星星、月亮、太陽》(合譯)、《傳說的高砂族》(英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