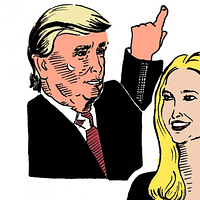劉曉波去世了。我生命中最寶貴的一部分也隨之而逝。
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三日晚上,我在唐山書店舉辦《拆下肋骨當火炬》的新書發表會。我最後分享的一句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這個蘇格拉底和顧準都使用過的典故,也是劉曉波一生的實踐,劉曉波就是拆下肋骨當火炬,照亮六四屠殺之後漆黑的中國。說到這裡,我心中隱約有不祥的感覺。
會議剛結束,我打開手機,巨大的打擊像石頭一樣砸過來,「曉波已經去了」,那是我最不願看到的一行字,我險些暈倒在唐山書店的樓梯邊,扶著墻才站住,一時間淚流滿面,恍若在夢中。
以殺人來維繫的政權再次殺人,多殺一個人對他們來說並不特別困難。接下來的幾天,局勢一天比一天險惡。並沒有因為曉波的死亡,共產黨就恢復了一絲自信。共產黨不僅害怕活著的劉曉波,也害怕死了的劉曉波。他們不顧劉霞的強烈反對,強行立即將劉曉波的遺體火化,不允許骨灰下葬在故土,匆匆實行了所謂的「海葬」。
當局安排劉曉波的大哥劉曉光在一場精心導演的新聞發佈會上露面,如木偶般説了一番「感謝黨感謝政府的人道主義安排,非常完美,非常周到」之類的鬼話。劉曉光還說自己是家中的大哥,家中的事情由自己説了算。他真是個法盲,劉曉波的事情難道不該由他的妻子劉霞説了算嗎?一個已經跟劉曉波斷絕關係將近三十年的陌生人,一個一度企圖瓜分劉曉波的諾獎獎金、得知劉曉波已經捐出獎金而無比失望並被劉霞基督鄙視的小官僚,有什麽資格取代劉霞第一親屬的位置?
難怪魯迅説,人最大的敵人或許是他的家人。宣稱沒有敵人的曉波,會料到他的大哥有這場可恥的表演嗎?劉曉波與劉曉光之間,除了血緣上的相同之外,再沒有別的相似之處。

劉曉波不是周恩來和鄧小平——周恩來和鄧小平是自己選擇「海葬」的方式,他們的骨灰汙染了大海。他們都是殺人如麻的屠夫,他們不敢下葬在土地上,他們害怕被後人鞭屍,他們更不願像毛澤東那樣成為一塊被風乾的「老臘肉」。
劉曉波「被肝癌」和「被海葬」了。這個「新納粹」或「超納粹」政權殘害劉曉波的生命乃至毀滅了他的遺體。以他們掌控的亙古未有的暴力機器而言,這樣做易如反掌。在此一事件中,共產黨果然無比信奉唯物主義——他們對劉曉波實行「挫骨揚灰」政策。只有當劉曉波在物理意義上「屍骨無存」了,讓友人和後人連追悼和紀念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接下來就是無邊無際的遺忘了,那樣共產黨才能真正安心。
當年,親人爲在文革中被殘害的林昭留下了一塊小小的墓地,那塊墓地就像是一道一直在汩汩淌血的傷口,人們絡繹不絕地前去祭拜和憑弔。當局不得不在墓地旁邊的樹上安裝攝像頭,並安排員警日夜巡邏,以恐嚇來自全國各地的林昭精神的仰慕者。這一次,當局吸取了教訓,他們防患於未然:沒有墳墓的劉曉波不會像有墳墓的林昭那樣,繼續成為黨國的大麻煩了。

然而,信奉唯物主義的共產黨絕對想像不到精神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有多大。劉曉波活在他的文字中,他的文字是不可戰勝的、無法消滅的。這些文字中蘊藏著自由的密碼,如同鑰匙,如同解藥,如同翅膀,可以幫助那些迷路的人回家,酣睡的人甦醒,沉淪的人飛翔。每一個字都是一粒麥子:麥子落到地上,死了,又結出許多籽粒來;文字印刷在書上,書是焚燒不盡的。由劉曉波的文字彙集而成的每一本書都是一束強烈的光,讓在黑暗中跳舞的老鼠驚恐萬分地逃遁。 (相關報導: 閻紀宇專欄:70多年前的「劉曉波」一個納粹囚徒的故事 | 更多文章 )
*作者為旅美作家,著有《我無罪:劉曉波傳》;本文收入八旗文化即將出版的余杰新書《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