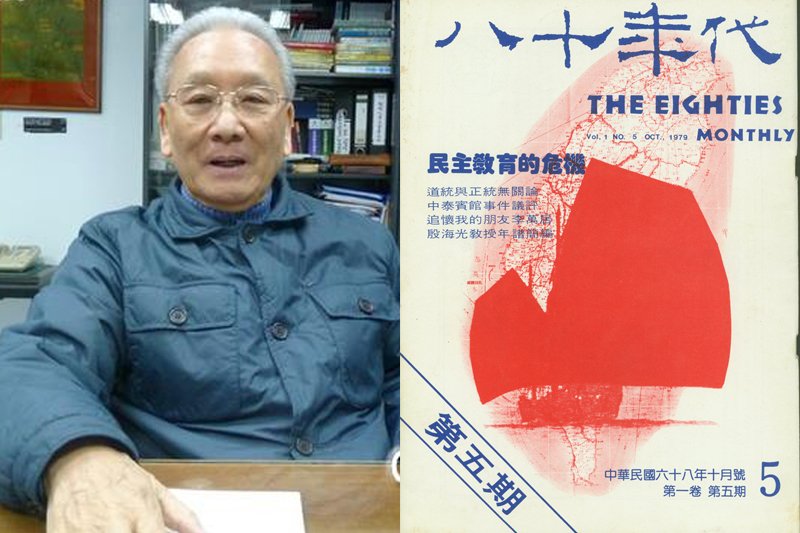我們來印禁書
在那禁忌的年代,馬克思、列寧等名字是禁忌,連許多姓馬的都遭殃。傳說陳映真被逮捕的時候,偵訊人員就問他:你家裡為什麼有馬克吐溫的書?
啊?被問者茫然了。
「那馬克吐溫不是馬克思的弟弟,不然是什麼?都是馬克什麼的。這代表你思想根本左傾。還不趕快招認?」
此外,還有人從國外帶回來馬克思.韋伯的書,在機場也被查扣了。原因是:他怎麼也叫馬克思?
機場當然是一個進口書的管道。英文書還好,有些新左派的書,負責把關的人不求知,當然不知道。於是陸續有些新書帶進來。但中文書,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學書,就很難帶了。於是我們有朋友想了不少怪招,讓香港的僑生帶回來。例如,把原書的封面給撕下來,再買一本瓊瑤的書蓋上去當封面。機場不查內容,就這樣蒙混過關。那時,曹禺的劇本、艾青的詩集、沈從文的自傳,都是這樣「表裡不一」給帶進來的。

我手頭上有一本封面是「死亡與童女之舞」,還是詹宏志翻譯的,內容卻是曹禺的劇本。詹宏志大約沒料到,當年他的封面也被我們「利用」過。
因為是禁忌,得來特別困難,我們也讀得特別起勁,有如在練功。彷彿擁有秘笈,再加上苦練,終有一天要練就一身絕技。
看禁書與玩禁忌的愛情一樣,是會上癮的。你越是要查禁,我越是要看。而且越禁越要偷偷摸摸,越偷偷摸摸,越是有趣。
現在回想,才知道影響自己最多的,可能不是那些學校規定的書,也不是正經八百的書,而是禁書。沒辦法,禁忌之愛,永遠有致命的吸引力。
由於大學生愛看禁書,買的人多起來,於是就有人開始偷偷翻印禁書。最初是台大附近傳出有人翻印外文書,後來政大那邊也傳出三○年代的文學選集,如魯迅小說選、冰心、丁玲等作品。那年代的學生較貧窮,在學校賣書可以賺一點外快,許多學生本來是幫正常出版社賣一些上課參考書,後來就乾脆賣起了禁書,而利潤似乎更大。

朋友之中有腦筋靈光的,動起了翻印好書,兼賺外快的想法。最初是找了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出版社「全國出版社」,老板是一個面貌忠厚的人,知識上不是太靈光,但人很好相處。至於出什麼書,大家一片熱血、熱烈討論後,決定以思想經典為主,第一批翻印的是大陸時期出版的書,張佛泉的「自由與人權」,以及卡西勒的「國家論」,還有一本是新書,林毓生的英文著作「儒學的危機」。
我只記得大家拿到新書的剎那,興奮莫名,有一種幹「地下革命」的快感。後來還有人建議海耶克的書,但似乎是老板對我們要出的某些書有意見,大家失望之餘,就少見面了。至於書賣得怎麼樣,誰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