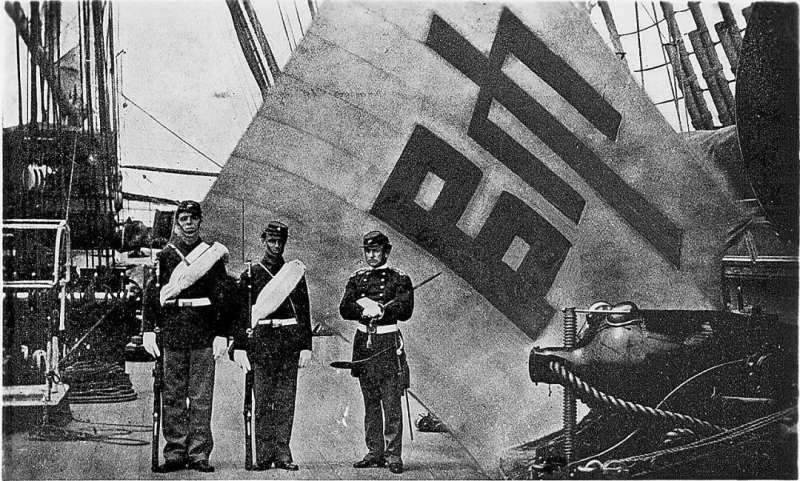
劇情發展至此,觀眾的情緒跟著陷落於失敗者的悲情,然而底下的一段少年皇帝和圓滑頑固的老臣對話才令觀眾驚覺見識、意識形態落伍的當權者是不可能從敗戰學到教訓的,這個國家的命運沒有可能更好, 只有更壞, 但到底會有多悲慘? 劇作家埋了許多伏筆。
大院君向年少的高宗宣布全軍覆沒, 高宗問,「所以我們輸了,是嗎?」
大院君答辯,「對方贏得空虛, 我們輸得實在。」
即使輸了也雖敗猶榮,官員還想以語言弔詭來掩飾無知顢頇。

交叉對照朝廷大臣的舉重若輕、實問虛答,在江華島前線被俘虜的降軍生死未卜,當美軍通譯官宣佈朝廷根本不管俘虜死活,反倒是美軍無條件釋放戰俘,原本和父親並肩奮戰的俘虜張獵人心理逆轉,決心不再效忠國家,立誓作個反抗朝廷的逆賊。
被國家背叛的戰俘的決定等於打了傳統忠孝節義一記巴掌:不能保護自己人民的國家有資格叫人民來保護國家嗎?
即使觀眾認定這只是一個父親戰死、憤世嫉俗的少年悲憤之餘下的決定,劇作家並未放過另一個針對社會不公平結構的尖銳提問。
男主角崔宥鎮,一名九歲偷渡美國的朝鮮奴隸,之後以美國軍人的身份重返朝鮮,他對極力想阻止朝鮮被列強併吞的命運的義民領袖貴俗之女愛信質問,「閣下想要拯救的朝鮮可以讓誰存活?」「可以讓貴族存活嗎?」 「可以讓奴僕存活嗎?」「還是可以讓白丁存活?」
《陽光先生》故事時間線主要從1905年拉至1910年「日韓合併」五年間,當時的朝鮮,官員腐敗貪污、西方列強環伺,西化成功的日本咄咄逼近,每一次外交衝突事件都削弱朝鮮主權, 將人民的生計一步步推入險境。 在這樣詭譎動盪的年代,以儒家朱子學說為中心理念的李氏王朝訂立嚴密分明身分制度,社會階級僵化,皇族、文武官組成的兩班、平民和農夫和最底層的白丁永遠壁壘分明,兩班以下的階層無法受教育,白丁賤民階層沒有姓氏沒有戶籍,永遠不可能從社會底層翻身。即使1894年正式廢止奴隸制度,但一直得等到1909年日本殖民政府設置朝鮮總督府,並導入戶籍制度,不被當成人對待、沒有姓氏的白丁等等各類賤民們才獲准擁有姓氏和戶籍(註3)。
崔宥鎮, 如果不是逃到美國, 留在朝鮮就連算得以保命,也將繼承父母的奴隸身份;就算有過人的才智體魄, 他依然沒有希望開展一個不同於父母命運的人生。就連個人基本自由也被剝奪,遑論晉身為代理美國公使的統治階級;因此他代表廣大的百姓發聲格外有說服力:一個階級僵化的社會就算將列強驅離國境,對他的子民又有什麼好處?這是劇作家對舊時代壓迫人民的社會制度的批判。台灣或中國的的歷史劇多半標榜忠君愛國,頂多有生不逢時,聖人不出、賢君未降的感慨。聽不到從平民角度質詢既有的社會結構、階級意識;當然在今天言論自由更受箝制, 中央集權的中國更不可能出現類似台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