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和這一票大牢裡關出來的兄弟做的就是這種買賣。李亞偉、老家、胖子等等,都是這個路子。他們互相幫忙,賺錢謀生。行有餘力,還可以幫忙受難的兄弟一把。
像劉曉波出獄沒錢生活,他又是一個書生氣的人,不會找生路,也不願白受人幫忙。於是野夫幫他想了一個辦法:做一本書。
他找了王朔和劉曉波對談。談的內容從文學、小說、藝術到文化現象,內容極是龐雜精彩。但劉曉波不能出面具名,他是被禁的作家。於是野夫幫他取了一個無人認識的名字「老俠」,王朔則幫書取一個古怪的書名,叫《美人贈我蒙汗藥》,靠著王朔的大名,書大賣。王朔義氣,稿費分文不取,全交給劉曉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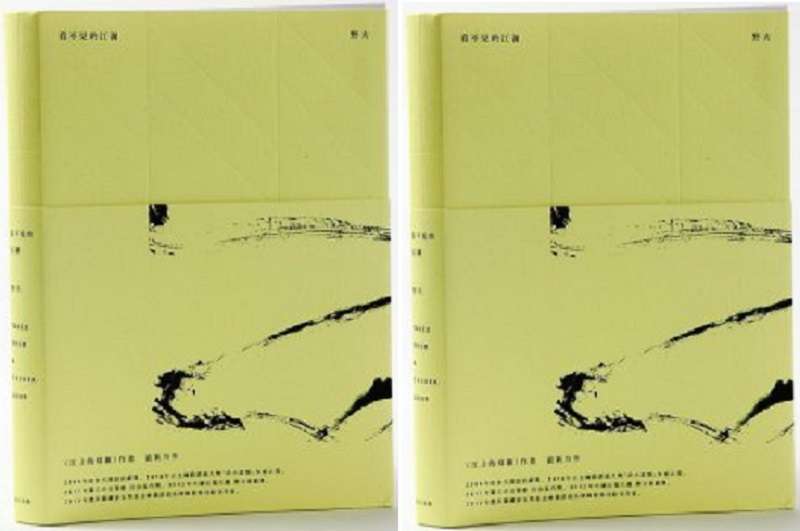
這事,若非野夫一手操辦,他自己說出來,誰也不知王朔這個「一點兒正經沒有」的人,竟有這一等一的俠客義氣。(王朔與劉曉波事,精彩萬分,此處所述不及萬一,敬請參閱野夫著作《看不見的江湖》,南方家園出版)
這就是北京的地下出版世界,一個「看不見的江湖」。
我們在北京相遇,酒酣耳熱之際,談著北京的地下書商與出版,便談起台灣的出版。我於是聊起當年台灣年輕人如何看禁書,搞地下出版,開了閱讀風氣,從而打開了一個開放社會的門。
「兄弟,莫說你們現在的地下書商無用,只是賺錢,這個地下社會是可以改變世界的」。這大約是我酒後說的。接著又說了幾個台灣禁書的故事。
當然,我們也不免談到台灣的民主化過程,與這些禁忌的逐步開放有關。那時,北京友人對民主改革滿懷希望,總期待從台灣找到一些借鏡,或者台灣人努力一點,證明中國人也是可以實踐民主理想的。
便是在酒後的快意中,胡說了一些故事,他們大感興趣,笑說:「你何不寫出來,給大伙兒看看,台灣是怎麼走過來的。」
那時,錢鋼正在主編《南方周末》,也有一幫朋友在那裡做事,於是想寫了給他刊登。作用是給大陸的友人打打氣,說明社會的開放總是有一個過程,它不是靠政府施捨的,而是像擠門縫一樣,慢慢把門擠開來,開放社會才逐步來臨的。
於是,我寫了「禁書的故事」,發表於《南方周末》。
這便是這個《禁書的年代》的緣由。

如今,北京地下書商的世界早已風流雲散,夢醒時分,各自流浪到大理、成都、哈爾濱、香格里拉、西雙版納、清邁等地,寫書、寫詩、種茶、談戀愛,亂世流放,只留下記憶中的江湖。
我也以為禁書對開放的台灣社會已是昨日黃花。卻不料,三十幾年後,當年搞禁書的某些人,做地下刊物的黨外人士,如今當了權,竟還想搞查禁書刊,而且用錢用力控制媒體,關電視台。最令人瞠目結舌者,戒嚴下,當政者還知道心虛羞恥,如今是堂而皇之,喊著反共的口號,硬生生把「紅帽子」當血滴子,跟1950年代白色恐怖沒有兩樣。
於是,我想起這一篇禁書文章,便拿出來和朋友分享。
回顧著禁書歷史,也想想,台灣的開放社會是怎麼來的,還要再回去嗎?回得去嗎?門還可以關得上嗎?
重刊出來也不是想提醒誰「莫忘初衷」,我對權力者不抱期望,而只是想在回顧中提醒自己,和還願意相信理想的人:「哪,你看,戒嚴下都不怕了,現在要重新搞禁忌,那就重來一次吧!」
無論如何,地下社會,比地上世界危險,但有趣多了!
*作者為自由作家。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