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通過母親、妻子、女兒三代女人徹底認識一個完整的女人。但女兒們好像並不是通過老爸認識男人。當她們評價男人時,可能把老爸當作同黨,因為太親密,親密得無視父親的性別。
我沒有女兒。
讀《我最親愛的》,寫的是女兒。怎麼最親愛呢?聽說有人寫女兒而成名,或者把女兒寫出名,那必是親而愛,但引不起我的興趣。對此書格外上心,因為是陳浩寫的。也讀過他的《一二三,到臺灣》,兩本書彙集的文章都是寫他和兩個女兒——「父女一場,十分愉快」。我讀了也十分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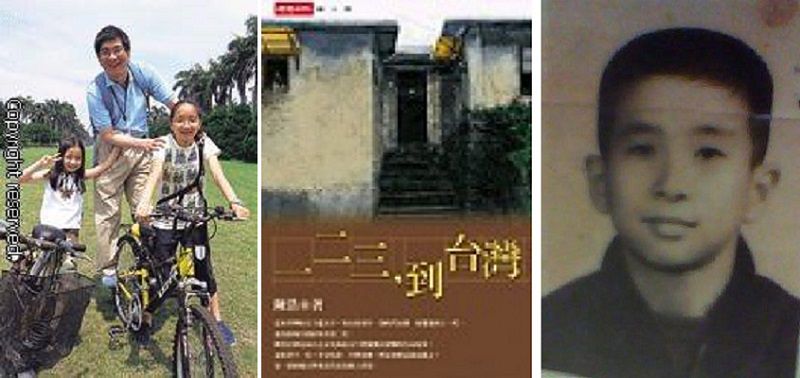
陳浩,臺灣那裡叫他浩子,傅月庵叫他浩哥,我也跟著叫,其實他倆比我小得多。要是拜把子,我老大,但是說為人行事,浩哥真是哥。我們相識,冥冥之中有一種鄉情。他寫道:「長春圍城,父親人在瀋陽,心焦如焚,東北大學師生決定撤往北平,他丟個銅板決定去留,命運讓他向南走,身無分文,作了流亡學生。他在臺灣去世二十多年後之後,有一天老三說,民國七十幾年,父親與老家裡的人通上信,才知道當年爺爺與家人早一步逃出城,到鄉下躲過一劫,長春圍解之後爺爺還與大爺到北平尋過父親,但悽惶流亡的隊伍也已散,父親同學幾十人南下去到了湖南。這都是四十年離亂,生死兩茫茫的上一代的故事,我們弟兄仨聽到的都是片片斷斷,從來也沒湊起來拼圖。」余生也晚,沒趕上長春圍城,上世紀60年代聽老一輩「憶苦思甜」,說那時困卡子,真有賣人肉包子的。圍解之後我父母從哈爾濱南下長春,我就自民國三十八年在長春土生土長,而陳浩的父親再也沒能回故鄉。
看來臺灣畢竟小,我居然結識了好多名家。多數好酒,即便是初見,喝起來也不拘束。有幾位年輕時寫詩,陳浩也「有過自列於寫詩族的蒼白歲月」,給迷戀的女生寫過很多詩,她看了半天,說:「看不懂呀!」也有始終是詩人的,初安民今年春天還曾在舉杯之間給我寫了一首詩。我敬佩臺灣朋友們,例如傅月庵,好讀書,是個讀書家,也常寫書評,正兒八經的書評家,偶爾寫小說,就是小說家,真是想做什麼成什麼,可我總說要寫小說,但寫寫小文章就已經吭哧癟肚。沒讀過浩哥的詩,多少知道他的經歷都是從別處讀來的。我交友就喜歡這種「案發現場」的感覺,頗有點英雄不問出處的意思。他自己寫道:
「我年輕時,追隨司馬文武(江春男)在《八十年代》雜誌擔任過兩年的編輯,後來進中國時報作記者,依舊為‘八十’以及各種黨外雜誌長期供稿。我戲稱同事的田秋堇、劉守成、廖仁義、康文雄等是《八十年代》二期畢業,美麗島事件前的編輯群如林世煜、周渝、林濁水等是如黃埔一期的前輩……
我永遠記得剛進《八十年代》時,江春男就先帶我與劉守成去洗三溫暖,說得有點像入社儀式或河中領洗,反正是男子漢裸裎相見,互信以誠。劉守成與我都很當一回事,我永遠記得當時與守成的一段對話。
『浩子,你為什麼要來八十?』
『大時代的變化就要來,這麼澎湃,我不想置身事外,但我的志向是像司馬一樣當個終身職的記者,我來黨外「參與觀察」。你呢?』
劉守成的答案比我乾脆:『我來參與黨外運動。』
三十多年來,我們都在當初‘『盍各言爾志』的道路上走,劉守成幹到兩任宜蘭縣長,治績有目共睹,我怎麼兜怎麼轉,都在媒體的範圍裡。血管裡流著還是記者Journalist的血,新聞人的魂魄。還是冷眼看著舞臺上的政治人物,成敗腐朽。基本不投票,除非是小女兒拉著我的手,一種公民教育的心情,才去做個樣子。(還很難跟他們解釋我心深處的那把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