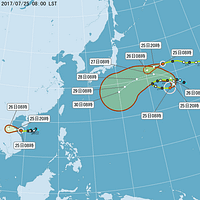第一次見到袁凌,我就想起那種古老的中國傳奇故事裡,經常描述有一種「骨格精奇」的人,全身嶙峋的線條會先映入眼前,形狀比血肉先看到。隨著他精氣神中帶著一種古怪的批判性質,幾乎是第一時間你就能感受到,這是個「人不驚人死不休」的傢伙,以後不知要生出多少是非。後來的事情,證實我的直覺果然非常靈驗。
老袁是我在北京《財經雜誌》工作時的同事,大概是我們辦公室裡得獎最多的人,平日不太瞧得起庸俗的記者,至少不愛跟我講話。他做了著名歷史學家高華生命晚期的採訪,高華以《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揭開早期中國共產黨內的權力鬥爭是如何奠定了中共的意識形態路線,在知識界是偶像級人物。
袁凌能在高華癌症末期、日薄西山之際,讓大學者點頭願意會面,這是為中國留下了重要的紀錄。高華離世後,袁凌重建了他的學思歷程,也因為這篇作品,得到了當年騰訊新聞獎的年度大獎。即使老袁得獎無數,往來都是柴靜這樣等級的中國一流記者,甚至在柴女神著名的霧霾紀錄片《穹頂之下》構思之際,參與了影片呈現的討論;以他的地位,大可以過著輕鬆的生活,找個大編輯的位置坐著,開始一天到晚教訓後生,消費過去,從此不思長進。可是他沒有。他喜歡跟自己過不去,那身精奇的骨骼突出在這世界就是格格不入,找不到一個舒服的位置。

袁凌震驚世界的報導發生在二○一三年,一個傳說多時卻從無證據,位在中國遼寧省瀋陽市,專門對法輪功信徒施暴的酷刑監獄「馬三家女子勞教所」,在袁凌長年鍥而不捨、一點一滴的追蹤下,終於第一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女囚在其中長年受虐,老虎凳、電棍、死人床等,各種我們曾經聽過的戒嚴時代酷刑,在馬三家裡肆無忌憚,受刑者因此重度殘廢、失去生活自理能力,連大小便都無法控制。就在離文明世界那麼近的地方,有人正在日夜承受暴行,讀者很難不為之落淚。
報導一出,國際媒體爭相轉載,震撼全球,傳聞多年的法輪功虐待場竟然是真的。由於和袁凌的私交,我知道這個調查有多不容易,是如何費盡千辛萬苦才能找到證據;然而他在公司裡的處境,卻突然變得異常尷尬。我們刊登那篇文章的、財經雜誌的子刊《 Lens 視覺》雜誌,遭到了官方最嚴厲的懲罰:撤銷刊號。
這在中國等於被禁止發行。幾經周折,社方才找到處理辦法,《 Lens 視覺》雜誌也停刊了一段不短的時間。停刊期間,袁凌在公司備受煎熬,同事們有些力挺,有些徬徨失措,不無怨言。畢竟這是人性。
袁凌後來的寫作生涯,就是以如此的曲折為主基調,總是一個大型敏感報導問世,他在公司裡就變得尷尬異常,儘管這些文章為他任職的媒體帶來風光無數,卻也不斷惹來麻煩。因此我總是聽到老袁又因為寫了什麼東西惹禍,不得不暫時休假的消息。上一次是去年,他在香港出版《秦城國史》,集結近十年來對專門關押中共高官的「秦城監獄」的調查資料。書才出版,一如預料,他又被要求暫時離開工作崗位。我聽到消息時,心情為之黯然。 (相關報導: 與黑道共枕,執法人員與黑社會的勾結:《出賣中國》選摘(4) | 更多文章 )

時而危險時而安全,還是要繼續寫下去
二○一三年以後,調查新聞在中國被大力打壓,財經雜誌最出名的「法治組」悍將為之一空;加之以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的經濟打擊,我眼見自己的老同事們一個一個離開了新聞崗位。有人去企業做公關、做董事長特助;有人做了創業公司,其中不乏成功的例子;有人乾脆回家當全職爸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