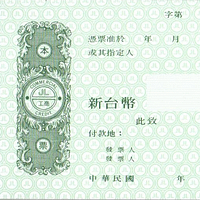上帝為了人類的罪惡而存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選摘(1)
劉曉波表示,這本書可以幫助自己恢復因悔罪所造成的心理傾斜,在某種程度上擺脫犯罪感的糾纏,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懺悔是自我拯救。(資料照,AP)
「從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在紐約的登機回家,到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深夜十一時左右被捕入獄,算算只有四十九天的時間,但這時間卻是我三十四歲生涯中最驚心動魄的日子,每每想起,覺得那麼漫長而幽深。它是我靈魂中的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三十四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劉曉波
這本書只是我個人的記憶和心態,並不能準確地再現「八九抗議運動」的全貌和深層心理。它所提供的僅僅是一個角度。
記憶總是有選擇的,淘汰一部分,保存一部分。而能夠保存下來的部分也肯定被整理過,某種程度的變形乃至歪曲是不可避免的。
儘管這本書帶有我個人的性格、侷限和偏見,但我決不掩飾這一切。純客觀是形而上學的假設,可惜得不到任何證明。我能做的就是盡量忠實於我自己的體驗。
如果書中的記述有歪曲事實之處,懇請其他當事人出面澄清,這也是對我的幫助。
本書的初稿在一些朋友中傳看過,他們的意見給了我各方面的啟發,有些接受了,有些拒絕了,但無論是接受還是拒絕,我都感到友誼的可貴。我想把這些意見公開,讓讀者自行判斷。
有的朋友幾乎毫無保留地肯定了這部稿子,認為它是到目前為止關於「八九抗議運動」的眾多文字中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它的真誠、它的嚴厲的自我剖析和對這運動的夾敘夾議的描述,使人們看到了「八九抗議運動」的本來面目。
有的朋友認為這本書對我自己的評價不客觀,殘酷到失去了起碼的公正,懷疑我是否有精神自虐症。所以說我對「八九抗議運動」的評價也必然不公正。「八九抗議運動」不是上帝的作品,不可能盡善盡美,我不應該用一種聖潔化的尺度來苛求它。從來沒有搞過大規模民主運動的中國人能夠達到「八九抗議運動」的水平已經相當不錯了。運動的意義決不像我所認為的那樣消極,灰色調不是運動的基調。
最後一種意見尤為尖刻,我剛剛聽到時真如五雷轟頂。這種批評不是針對書中關於運動本身的記述,而是直指我對自己「悔罪」的懺悔。這位朋友說:「你的懺悔儘管讀起來頗有震撼力,但這是不是一種更高級、更巧妙的自我解釋和自我辯護,甚至是不是另一種方式的偽裝。你不是基督徒,懺悔從何談起。就連基督徒的懺悔都有虛偽的成份,何況我們這些根本不理解神聖價值為何物的人呢?」
我寫了這本書,並決定公諸於世,自然認為它有獨特的價值。否則的話,或乾脆不寫,或親手燒掉。我做不了卡夫卡式的作家。他曾在病中囑託一位最了解他的作品的價值的朋友燒掉其手稿。我不懷疑卡夫卡的真誠,但我認為這僅僅是意識層次的真誠。他的潛意識知道他的朋友不會毀掉那些手稿,因為他的朋友知道這些手稿的寶貴價值。如果卡夫卡真想把自己的作品付諸一炬,何不親自動手?
這本書還可以幫助我恢復因悔罪所造成的心理傾斜,在某種程度上擺脫犯罪感的糾纏,無愧於自己的良心。懺悔是自我拯救。
但是,懺悔也有其邪惡的一面。上帝為人類的罪惡打開了一道暢通無阻的後門——懺悔,任何罪人都能因懺悔而得到自我的良心解脫和上帝的寬恕。同時,懺悔和真誠還能感動無數旁觀者,使他們由憎恨而憐憫,覺得此人儘管罪惡滔天,但還真誠,還有救,還能從此棄惡從善。懺悔是人類的另一種自我塑造。當人類求其完美的自我形象不可得時,就用懺悔來裝飾其弱點。這樣,會使人做起惡來也心安理得,因為人有退路了。
一個雙手沾滿他人鮮血的殺人犯,他的懺悔所贏得的原諒和寬恕是不是罪上加罪呢?人為什麼非要等作惡之後才懺悔,為什麼不能從一開始就不作惡呢?不作惡就不必懺悔。但是,這不可能。人性自有其惡的一面,犯罪從人類誕生之日起就無法避免。罪人除了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外,還要承受道德審判。減輕社會的道德壓力的最好方式就是懺悔。特別是那些能夠超然於法律之上的大惡人,唯有通過良心發現和懺悔自責才能獲得靈魂的解脫。每念及此,我都有一種生而為人乃最大恥辱的感覺。十全十美的上帝卻創造出罪惡纍纍的人類,豈不是莫大的諷刺。在心理上彌合這一裂痕的辦法只能是懺悔。完美的上帝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垃圾筒,懺悔就是清潔工。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完美,更沒有人能像上帝那樣容忍罪惡。只有上帝才能超然於人類之上,以寬容的態度無限制地接受人類的一切罪惡。換言之,懺悔使上帝成了裝載人類罪惡的無底洞。
如果這世界沒上帝,人類也會變得聖潔,既不作惡也不懺悔。但這僅僅是「如果」。沒有上帝,人的犯罪便毫無意義,上帝就是為人的罪惡而存在的。
那麼,人類只能在兩種現實中進行選擇:要嘛是有上帝、有罪惡,也有懺悔的世界;要嘛是只有罪惡而沒有上帝,也沒有懺悔的世界。
更多新聞請搜尋🔍風傳媒
因為你,我們得以前進,你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
更多文章
觀點投書:蔡總統,最昂貴最奢侈的超跑也有脆弱的一面蔡總統在815大停電隔天的中午,停電發生20個小時之後,在民進黨黨部發表讀稿機式的道歉聲明。她在聲明中,用厚黑式的一個話術輕鬆推卸了整啟事件的最終責任。她說:「台灣所面臨的問題,在於電力系統脆弱,現在會因為天災或人為疏失就輕易癱瘓的電力系統,才是應該全面檢討的問題核心。」
張若羌觀點:用帥打仗的國防部 台灣天空最近很忙。中共解放軍的各型軍機,藉遠海長航訓練,三天兩頭繞行台灣展示軍力。我空軍則是被軍事迷拍到,飛官把F-16戰機當貨機,運載花蓮名產麻糬到高雄。兩相對照,兩岸空軍戰力孰優孰劣,不言自明。一葉知秋,麻糬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當前國軍早已百廢待舉,主事者卻任其凋零。
觀點投書:全部科目免試取得專技人員執業資格,公平合理嗎?現行國考制度中存在著一個既不公平、又不合理之全部科目免試制度。簡言之,具有特定學歷條件,並經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特定類科及格,分發任用後,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擔任與考試類科相關工作3年以上,成績優良,有證明文件者,得申請建築師、技師、地政士等全部科目免試。此一制度有其法理上依據,包括: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第13條:「(第一項)具有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相當之學歷經歷者,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得視其不同學歷經歷或具專業技能證明文件,為下列之減免:一、應試科目。二、考試方式。三、分階段或分試考試。(第二項)前項申請減免之程序、基準及審議結果,由各該考試規則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考選部得設各種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辦理本法第十三條申請減免應試科目案件之審議。」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組織規程第8條第1款:「審議委員會審議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經核定准予全部應試科目、考試方式、分階段或分試考試免試者,由本部報請考試院發給及格證書,並函相關職業主管機關查照。…」所以專技人員全部科目免試制度,可以說是雖然於法有據,但情理上似欠妥適且有違公平原則的一種制度。
觀點投書:加薪不是解決勞工處境的唯一方法最近幾起勞資爭議的發生、政府態度趨向曖昧不明,近日全聯傳出員工因加班過勞而過世,更引發民眾對血汗勞動環境的怒吼。同時面臨著物價飛漲、低薪的台灣,勞工似乎看不見未來,對於工作環境如何發展,問題該如何解決,有論者提出不少解方,而綜觀也發現可分成下列兩種說法:
永豐金董事長何壽川4億元交保 每天向派出所報到永豐金董事長何壽川因涉入永豐金違法放貸案,與永豐餘土地開發部經理張金榜及三寶建設董事長李俊傑之妻廖怡慇同被收押。台北地檢署今(17)日偵結,起訴永豐金前董事長何壽川等19人,台北地院裁定,何壽川4億元交保;另外3被告,廖怡慇5000萬、永豐金秘書室經理陳佳興1000萬、張金榜100萬交保,4人皆限制出境出海與住居,何壽川每天要向派出所報到。
又停電了!線路跳脫 北市萬華6727戶停電 815全台大停電,台電將責任歸給中油,中油則和包商之間互相指責。今(17)日晚間9點5分因線路跳脫,台北市萬華區西園路、萬大路一帶又停電,台電表示,共計6727戶停電,1901戶已復電。
從義大利回到台灣,聖火暫駐的「毛公鼎」也有來頭2017台北世大運19日將開幕,聖火傳遞活動也於今(17)日正式劃下句點。聖火自台北市長柯文哲於義大利杜林引燃聖火母火後,經拿坡里、韓國大邱等旅程,今天下午回到主場地台北田徑場,暫駐53歲的「毛公鼎」駐火台,等待開幕典禮到來。
大巨蛋案法官壓力大!左籲柯文哲「想開了就很容易」 右指遠雄「錢不要賺那麼多」遠雄大巨蛋於2015年5月20日遭北市府以違反《建築法》58-6條為由,勒令停工,遠雄認為行政處分違法,不滿提告。17日上午,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展開北市府與遠雄兩造言詞辯論,審判長黃本仁在場提出雙方「和解」的建議,還建議雙方律師把話帶回去,這兩天「考慮看看,請示一下」,「大家都有面子,也有裡子」。對此,遠雄建設總經理湯家峯表示,「若市府撤銷停工處分,我們也送件審查」。
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入獄 國際特赦組織:港府惡意追殺、秋後算帳香港法院上訴庭17日宣判,「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主席羅冠聰和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三人非法集會罪成立,分別入獄6個、8個月及7個月,即刻入獄,成為香港首批下獄的政治犯。對此,國際特赦組織發布聲明表示,今日判決是「惡意攻擊言論與和平集會的自由」,香港表達自由雪上加霜。去年8月,香港法院就2014年9月「重奪公民廣場」運動,裁定黃之鋒和周永康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立、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立,分別被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毋須入獄。但是港府律政司不滿刑期過低,聲提出刑期覆核,要求改判三人監禁,為日後示威集會衍生的罪行定下量刑指引。根據香港法規,3人因為被判3個月以上徒刑,5年內將無法參與立法會或區議會選舉,政治生涯被迫中斷。3人中年紀最大的是周永康,26歲;羅冠聰與黃之鋒各只有24歲、20歲。
杜絕「假開工」,柯文哲下令木柵公宅24小時內施工台北市長柯文哲今(17)日主持木柵公宅開工典禮,表示木柵公宅「雖然不是豪宅的價格,但看起來像豪宅」,並表示北市府規定決標後3月內開工,也為了杜絕過去「假開工」文化,規定開工24小時內推土機與機具一定要進場施工。
「註記平埔族人數可能超過55萬人」原民會:民眾可向戶政機關調閱祖父輩戶口名簿行政院院會今天通過《原住民身份法》草案,原民會主委夷將・拔路兒表示,根據日治時代的人口統計,當時被註記為「生番」與「熟番」的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在日治時期人數為3萬3千多人,具「平埔」註記的人口則高達4萬6千人,以目前台灣原住民族人口55萬人推估,未來新法通過後,平埔族的身份確認必須經戶政機關登記,如果平埔族人的自我認同很強,未來註記為平埔族的人數,有可能超過55萬人。
行政院組改大戲上場,海洋委員會明年成立 確定落腳高雄行政院組織改造,在九月開議的立法院會期將是重點法案,目前包括國家公園管理處、漁業署、林務局,到底要不要併入環資部,過去一段時間,已經出現搶人大戰,在行政院院會今天通過廢止《蒙藏委員會組織法》後,行政院人事總處下午也宣布,「海洋委員會」明年4月正式成立,並且確定落腳高雄,根據行政院內部規劃,由於高雄市在爭取海洋事務方面十分積極,包括科技部國研院「海洋科技研究中心」,經濟部的海洋風電專區,都已落腳高雄。
黃之鋒等遭判入獄 民進黨:愈嚴厲的壓制 只會激起愈多的反抗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等人因參與雨傘運動遭判刑入獄,民進黨17日晚發出聲明,表達高度遺憾,聲明也直言,愈嚴厲的壓制,只會激起愈多的反抗。香港民眾期盼爭取政治改革,獲得更多的民主自由權利,以此選擇自己嚮往的生活和制度,港方應正面看待之。
停電診斷》只有14秒反應時間…中油將全面檢視關閥與進氣口距離中油操作疏失,造成大潭電廠瞬間斷氣、引發全台大停電。中油董事長陳金德今(17)上談話性節目,談及15日意外,表示中油輸氣閥門離電廠距離實在太近,導致斷氣後電廠只剩14秒反應時間,才會一下子跳機,因此將和台電商量將肇禍的計量站移出大潭電廠。中油官員也表示,接下來不排除重新檢視全台所有天然氣電廠的天然氣管關斷閥,避類再發生類似情形。
「內政問題」!委內瑞拉回函言明棄賽世大運台北世大運即將進入開幕高峰,卻仍有多個國家報名不完整,據了解,目前為142國報名完成,但有填報意向書的國家有152國。委內瑞拉就屬其中一個沒有報名完成的國家,可靠消息指出,委內瑞拉以「內政問題」為由,表達要棄賽世大運,另,幾個非洲小國也可能因為沒有經費,而無法報名來台參賽。
國民黨團提「調閱委員會」查停電,柯建銘譏:就是要卡前瞻預算針對815全台大停電,國民黨立院黨團今(17)日決議,明天將在第3次臨時會提案,要求成立「跨黨派調閱委員會」,追查事實真相。對此,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柯建銘今晚表示,現在是臨時會,依法不可能在此時成立,他更酸「這專業知識有問題」,國民黨團很明顯是要「卡」前瞻預算案,國民黨團根本是「司馬昭之心」。
避免暴力集團濫用本票討債 金管會擬修法限縮裁定範圍本票作為民間商業往來工具,依據《票據法》,可以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對債務人財產強制執行,但多年來遭到暴力討債集團濫用,部分不肖雇主甚至逼迫外勞簽訂本票以防止逃跑,有鑑於此,監察院2年前糾正金管會,金管會17日公布《票據法》修正案,將裁定的申請對象限縮為金融機構擔任擔當付款人或執票人為金融機構之本票,金管會表示,由於本票在民間商業上使用範圍廣泛,為避免影響本票持票人權益,在《票據法》尚未完成修法以前,已簽發之本票仍可向法院聲請本票裁定。
世大運即將開幕,北捷這麼做提升反恐維安世大運開幕在即,台北捷運表示將提高反恐維安等級,將捷運各車站公共區不銹鋼垃圾桶改以透明塑膠袋方式替代,車站人員及捷運警察也已提高巡檢強度。北捷提醒旅客一起關注捷運系統安全,比賽期間也歡迎利用捷運至各比賽場館觀賞精彩賽事。
【今日國際特調】8月17日:泰國觀光客花錢蹲苦窯 歐巴馬推文成史上最多讚泰國曼谷旅遊業發達,有許多精品旅館,但也有些旅館走特別路線吸引客人,蘇克站青旅(SookStationHostel)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這間青旅打造監獄主題的住宿環境,提供條紋睡衣與身高刻度的背景牆,讓房客能拍出自己「嫌疑犯」照片,吸引想嚐鮮的旅客。飯店老闆說這個旅館的靈感來自於電影《刺激1995》(TheShawshankRedemption),儘管旅館營造出監獄的感覺,但許多房客說這裡的員工友善親切,環境與氣氛都很好。
2018台中市長選戰 預測看好盧秀燕戰林佳龍2018地方選戰將至,未來事件交易所日前針對台中市長選戰進行第一波預測,在台中市長林佳龍幾乎確定會競選連任下,預測國民黨潛在候選人對上林佳龍,誰最適合一戰。結果顯示,預測市場最看好的是立委盧秀燕,其次則是佈局多時的前立委蔡錦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