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錄音麥克風擱在桌前,劇作家還是不太習慣。紀蔚然60多歲了,曾經焦慮來襲時,紀蔚然會在講台上「跳電」,只能一手揪著大腿,一手繼續掛在黑板上,才把課上下去,如今拜小說所賜,紀蔚然填回遺忘半世紀的回憶,那些年少與陰鬱的往事,談起來總算能稍微坦然。
10年前,戲劇系教授吳誠再也受不了劇場界的浮誇與庸俗,在酒後怒罵中遞出辭呈,改行當私家偵探,這是小說《私家偵探》的開頭;10年後,寫出這個故事的紀蔚然也從台大戲劇系退休,如今泰半精力都在寫偵探小說,跟他的難兄難弟吳誠一起學著辦案,一起與心魔共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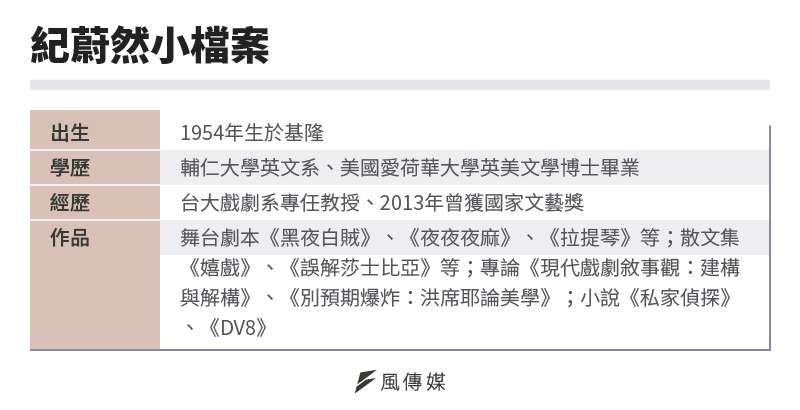
從吳誠的經歷,到字裡行間流瀉的焦慮與憤恨,《私家偵探》儼然紀蔚然的偽自傳。除了思索如何破案,吳誠大半心力用於對抗恐慌症,半數腦力則用於批判;他罵媒體與名嘴聳動、藝術家想像力稀薄、劇場走向空洞的懷舊與為批判而批判,失婚失業的落魄教授,住在殯葬業林立的台北臥龍街,希望就此逃離世界。
時隔10年,紀蔚然才從數不盡的劇本中脫身,以記憶中的酒吧為名寫了續集《DV8》,這回吳誠跟著他一起搬到淡水,揭開往日社會的陰暗;考慮到刑事追溯期的20年時限,故事裡時間只經過1年,但現實裡,紀蔚然又走過10個年頭,許多怨怒都已經沉澱。
其實這幾年間,紀蔚然不是沒構思過續作,但一來騰不出時間,二來構想總不滿意,退休來到淡水後,一日他讀到榮格的《人及其象徵》,突然間懂了要寫什麼,後來他回到年少成長的三重、蘆洲取材,望著昔日街道、母校徐匯中學,終於接起遺忘的記憶,帶吳誠跟他一起走上修復之旅。
過去,紀蔚然的文字以鋒利甚至尖酸聞名,外人看他像一把被壓抑的火,如今他的憤怒已慢慢淡去。幾年前,他在法國哲學家洪席耶(Jacques Rancière)的理論裡體悟藝術必須超越批判,「我不再那麼生氣,我知道罵也沒用,我再怎麼批評,都是沒有建設性的東西,後來心境一變,就都不想寫了;我對文學、藝術甚至對人,都有一些修正或改變。」

於是吳誠嘮叨的思緒有了節制,「之前他是個憤怒的人,想脫離整個社會,最後才終於慢慢回到社會,而隔了這麼久,我不必再處理他的憤怒,我寫的時候也不再那麼憤怒;是不是化解了我不知道,吳誠還是在處理他的精神疾病,但已經不再耽溺於個人,反社會情節淡化很多。」
小說寫到第2本,已有許多朋友跟紀蔚然說,喜歡《私家偵探》多過《DV8》,但他心中,《DV8》其實更為純熟。
從戲劇系教授半路出家當偵探,吳誠恍若紀蔚然的化身,是以在小說裡,紀蔚然對於自己的心理也毫無保留。《私家偵探》先花一半篇幅談吳誠心理如何掙扎,再花一半篇幅闡述如何捲入兇案、辦案,「辦案時心理不見了,不平衡啊,我不會特別喜歡,原因就是這個結構。」
劇本寫到得國家文藝獎,但寫起小說,戲劇泰斗坦言犯錯是因為沒經驗,到《DV8》終於慢慢上手,這次他已經把自身的矛盾攤平到各處細節,年少時因憂鬱症與友人疏離、逃離家庭與學校的種種過往,隨著吳誠查訪案件,逐漸放回作家跟偵探心中。 (相關報導: 紀蔚然專文:古早以前的天空並不藍 | 更多文章 )

「現在年紀比較大了,要稍微坦然一點。」那完全是紀蔚然的親身經驗,如今他也希望,能給走過相似歷程的心靈一點療癒;當年發作時,台灣根本還沒憂鬱症這個詞存在,更遑論相關療程,「那時跟家裡講,他們就帶我去看家庭醫師,只會開安眠藥給我。」
後來,紀蔚然在報紙上讀到有醫生談論心理疾病,於是瞞著家人偷偷去看門診,「那時真的很亂七八糟,百憂解還沒發明,他們也無法對症下藥」,於是每有症頭出現,他就往不同的醫院跑,跌跌撞撞之間,對各大醫院門診竟也熟門熟路。
紀蔚然:有意、無意分享跟恐慌症、憂鬱症相處之道
「這幾年憂鬱症變成大家朗朗上口,我也覺得要面對那些東西,順便回憶那時的心情。」誠然憂鬱症沒有所謂康復,紀蔚然依然要與心裡的黑暗拉鋸,規定自己走路出門、節制飲酒,試著平衡身心,「如果小說大家覺得無聊,至少能得到一點抗憂鬱的療癒,我是有意、無意地跟大家分享跟恐慌症、憂鬱症的相處之道。」
紀蔚然其實把《DV8》當日記來寫。他每天寫1000字,情節邊寫邊想,有時被害人出現,還沒頭緒誰是兇手,寫完發現要少了線索,再回頭補上,沒什麼太縝密的計算,連善、惡辯論也不想多管,「反正偵探小說就是正義,有人被殺,就要破案。」
紀蔚然也明白,當然有深入探討善惡的推理作品,「但我還是新手」,於是《私家偵探》有善構成的惡,《DV8》裡有偏執成魔的人性,但終究是推動故事的環節,兇手內心如何掙扎到成為扭曲地步,他不想多談,「有種寫法是讓他們說更多,但我不太想碰,可能有點害怕面對。」
面對生命慢慢坦然了,但講起邪惡,紀蔚然語氣變得遲疑,遠方依然有些污濁的東西讓他恐懼。幾年前,宏達電爆發內鬼案,首席設計師被控將機密技術竊往中國,紀蔚然看了新聞,見這人身材精瘦、身穿高領毛衣,理著平頭襯上斯文眼鏡,根本賈伯斯翻版,「我相信他家也一定很乾淨,但內在可能很黑或很亂。」
當紀蔚然把目光放在所謂年輕一輩,3、40歲的社會中堅分子時,心底竟蔓生憂慮,「他們職業都是白領階級,外表都是光鮮亮麗,面對社會要求可以做得很好,但底下的暗潮平常看不到,有種分裂的東西。」
紀蔚然回憶有次在網路上,看到朋友討論社會對不起年輕人,卻有年輕人說,要怪年輕人自己不爭氣,「哇,現在有人可以大言不慚,我成功因為我厲害,你不成功因為你失敗,我就懷疑他們的內在是什麼?可能是反社會;他們奉行物競天擇、幾乎沒有同理心,但你要他有禮貌,他就有禮貌,要環保就環保,越來越會隱藏,看起來都很雅痞、都懂得遊戲規則。」

「這一代人把反社會的東西隱藏得很深」
至今紀蔚然依然不懂這種分裂從何而來。「我們這一輩作家真的是髒髒兮兮、邋邋遢遢,講起話髒話連篇,喝酒就像野獸,現在碰到30、40歲年輕人,乾淨到像從無菌室走出來的,可以做環保、不抽煙、不講髒話,這麼乾淨,那他們內心怎麼樣呢?這一代人把反社會的東西隱藏得很深,我們的反社會是掛在嘴巴上,講完就算了,也算象徵性殺了人,回家就沒事。」
邪惡太污濁了,紀蔚然不敢碰,推理新手停頓片刻,才終於露出笑容,「其實福爾摩斯也這樣,從流派來說,福爾摩斯很少去寫邪惡、寫它的心境,所以我跟他一樣。」
1個多月前,紀蔚然終於有了臉書帳號,在連臉書公司都哀嘆自己退流行的今天,他還跟這個平台處在蜜月期,最初原因只是要跟網友筆戰戲劇,沒想到就此騎虎難下,索性寫起平常不太有機會談的語言學。
其實面對人這回事,紀蔚然還是不太習慣。紙本仍然盛行的時代,出書只要靠藝文副刊、文化版就夠打響名號,如今紙本式微、資訊爆炸,作者總得一場接著一場跑講座打書;紀蔚然說,這些事他還是不習慣,就是幫忙出版社,他偏好與人對談,公開演講敬而遠之,「你要有人問我東西,不然我們就大眼瞪小眼,坐在那裡。」
都當了25年教授,還怕對人群講話?紀蔚然搖了搖頭,「我有憂鬱症,選擇教書這個職業看起來有點矛盾,但從精神狀況角度來講,是最好的選擇,逼我每天要出門、逼我面對人,就要克服這個困難。」
這天紀蔚然又要面對人了。隨著《DV8》出版,這陣子紀蔚然從淡水河畔被召喚出來,到各個書店參加講座,有的談自己的書,有的是跨界對談,訪問結束後,紀蔚然下個行程便要前往誠品書店。 (相關報導: 紀蔚然專文:古早以前的天空並不藍 | 更多文章 )
「我要先去準備。」暮色已經染上街道,紀蔚然戴起帽子離去。所謂準備,是想在外頭走走、多繞幾圈,又坦然地寫過一段人生,要對人開口前,他仍得留點時間給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