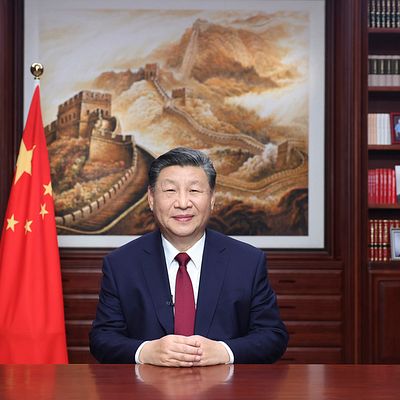書稿看似雜錯却空前繽紛:《拉波德氏亂數》選摘(1)
《週期表》整部書稿無可名狀,這卻是最妥貼的書名。(圖:取自pixabay)
翁勃薩不再。我凝望騰空的天色,自問:翁勃薩可曾真正存在過?枝葉交疊形成網孔,細密無盡,經過網孔篩過之後的天空只餘下飄忽光點,或許就是要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哥才可以過著鳥雀一般的生活吧。這般風景,就編織在一片空無之上。不禁聯想起我的書寫過程。我任憑筆墨在紙頁之間流轉,密集勾畫出刪節的記號、校正的字樣、塗鴉、墨漬,有時留白,有時妙語如珠,有時徒留星火般的微瑣點子,之後脫軌離題,在枝葉和雲彩上頭耗費太多字句,接著所寫過的文辭又交錯起來,向前騰躍,跑啊,跑啊,跑啊,霹靂啪啦奔放出最後一串沒有意義的詞彙、意念與空夢,最後故事於焉結束。
──伊塔羅.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
但我只再說一個故事,一個最神祕的故事。我知道生命的無常,語言之無力,所以我以謙卑自抑之情來述說。
它再回到我們之間,進到一杯牛奶,在一長鏈分子之中。它被喝到肚子裡。既然所有生命體,對外來生命結構都存有蠻橫的不信任,鏈索將細細拆解,碎片一一檢查,接受或丟棄。我們關心的這原子,通過腸壁進到血液,奔跑,敲到一個神經細胞大門,進門,提供了所需的碳。這細胞是在大腦,我的大腦,正在寫這本書的腦子。這原子所屬的細胞,所屬的腦子,正進行著巨大、不為人知的活動。此刻,這活動錯綜複雜的發出指令「是」或「不」,讓我的手在紙上規則移動,勾畫出渦形符號,一筆一劃,上上下下,引導我這隻手在紙上圈出這最後的句號。
──普利摩.李維,《週期表》
少年十六歲,母親不明白他的理想,擔憂他加入的社團:為了保衛祖國義大利,他們齊穿黑衫,攜自製「聖棍」,滿城挑釁亞非移工。母親命他,去見一位老人(母親的朋友),說他將開導少年。老人叫李維,猶太佬的姓,少年知道他,課本裡就有他的文章,講集中營經驗,沒什麼火氣,最不原諒的人是自己。少年讀了不喜歡。少年沒那麼笨,也花了番工夫做準備,見老人時,帶去一大疊資料,證明集中營內,從來沒有毒氣室。少年義憤填膺,責問老人:為何要一再誇大沒有的事情?少年罵得老人再無話可說,只瞇起霧眼,不知望著少年身後的什麼。
面對面,他們坐在老人書房裡。母親曾感佩說,朋友所有作品,都是在此完成的。少年游目四望,覺得這真就只是舊樓寓裡,一間即將不堪使用的陋室:書報文件凌亂堆積;牆面掛滿包漆銅線折成的猴子、蝴蝶或甲蟲;書桌上,竟有一臺新電腦,那最令少年感興趣。還能閒置的空間,就壓縮一股老人味。完全可以想像,多長歲月老人窩在裡頭,兀自夢遊。老人還是不回話,呆滯中,只剩每隔一會,書架後傳來的悶篤擊牆聲。少年現在有禮貌,靜靜聽候著。終於,像是給擊醒了,老人苦笑,抱歉說:那是老人母親在叫喚,她腿腳不好,需要照料。少年頗驚訝:老人母親,該是人瑞了吧?少年看他遲緩起身,想想自己母親,都油然有些同情老人了。少年有風度,默領此戰勝績,收攏茶几上資料,與老人握手告辭,先一步出書房。
(相關報導:
勇氣是最好的保護:《為幸福而生》選摘(1)
|
更多文章
)
服侍完老母再睡下,李維站陽臺,眺望細雪紛降大街上。他想起自己最睿智的朋友,卡爾維諾,已經猝逝年餘了。所以這些事,朋友無從知悉了:今日,一位美麗新少年,踏雪前來滅殺他。就在他勉力自持的溫室裡。今日,雪格外晶亮,像今春車諾比輻射雲,這才遲遲南來、摔裂成他所能見的,世上最後的冬天。有時,你夢想必定有什麼,是人可教會人,去深刻銘記的。但其實,人只給予彼此「可以毀滅的事物;可以燒光,可以侵犯,可以砍斷,可以摔爛,可以腐敗的事物」。有趣的是,這竟像是千言萬語裡,他寫過惟一正確的字句。
再過數月,冬雪將融,破碎的一切會再隨之緩流。這是他和智友的間隔。具體,就是一道冥河。
也給予他一艘船,必定,比小說家前輩(兼油漆廠經理)斯維沃更完善,他會將船漆髹得恆久如新。記憶,像攀附船體的盤管蟲,稚幼時隱形,水中漂蕩,執拗追索有機印記、溫度,或只是聲音的暗示。船那無論行止、總是恆定的軀殼,是太好的落腳處。為了落腳,牠們這才生出肉足;依附此足,牠們這才縱令自己生長,轉瞬變態為成獸。船殼包漆,是沉默的曉諭,明告記憶的幼蟲:汝不得現形、不可滋生。包漆,就是具體披覆的遺忘。
或許,在每道忘川之畔、每間修繕渡具的船塢裡,都還用得上,像他這樣的一個化學專家。
專業之一是編輯,多年來,卡爾維諾總是李維書稿首名讀者,和最入微的審查人。他私認李維,是「同胞弟兄,靈魂伴侶」。某天,他發現李維仿擬《樹上的男爵》,寫就新作尾聲。一九五七年出版,卡爾維諾《樹上的男爵》,結束在敘事者「我」,對自己書寫動作的同步描述中—當「我」的筆尖,釋下全書最後字母「i」上那點時,這整部追記「我」哥哥柯西謨傳奇一生(十二歲時他負氣上樹,立誓從此不觸地面、憑空生活;直到年老將死,他且隨熱氣球高升,實現完美消失)的小說,也就被虛構蹤跡給爆破,兌出自足的夢幻與泡影。
十八年後,李維追查一顆碳原子,在孤星上的環飛,看百年以來,它逼真的死滅與復活:曾在地脈,在礦工鋤尖的擊打,在窯焰,在煙塵,在翔鷹的血與肺;曾三次溶入冰冷海水並三度游離,也曾長長久久,被一束陽光給釘在一片葉子裡。直到此刻,從杯中牛奶,通過腸壁,它繼續奔跑,攝入神經細胞,在「我」腦中。它化出意念,驅策手腕,運轉筆尖,終結「我」對重重往歷的偵測與創造。
讀完新稿,卡爾維諾非常快樂,因彷彿亦是至此,他才能確信兩人友誼,得到這位害羞作者的認肯。以所能想像,最公開的隱密形式。因這位害羞朋友,同時也是頗武斷的讀者:他受不了卡夫卡以降,幾乎所有現代文學作品(使人掛懷的評語:他說保羅.策蘭的詩形同「欺騙」,就是「獨自赴死之人的語言」);但原來,他曾細心揣摩卡爾維諾,將對方手澤,延展為自己思路。
更重要的,是這般思路,所回溯的地景:書稿乍看雜錯,卻空前繽紛地,包羅李維半生場景,從油漆工廠,集中營實驗室,游擊隊刑獄,大學課室,到更早之前;以簡潔化學規律,所綻放的豐富文學性,再現個人絕少記憶的父祖從來—那半靈半肉、受召自聖靈暨塵土的人頭馬;那因戀愛受挫,從此立誓不下床的赤忱愛戀者。那些由「我」,親手餾除人世不免的重力、能量、運動與時間變數,才能還原的,天真的柯西謨們。《週期表》:整部書稿無可名狀,這卻是最妥貼的書名。
卡爾維諾非常快樂。因他感覺,這是朋友自己,可衷心接納的第一部書:從前寫作當然都衷誠,卻總回授作者更大不安,像被迫的代言,因此格外警醒著、深懼著自己可能的詐偽。彷彿,從集中營生還後整整三十年,朋友這才容許自己,在那死境裡,自由地漫行。
(相關報導:
勇氣是最好的保護:《為幸福而生》選摘(1)
|
更多文章
)
更多新聞請搜尋🔍風傳媒
因為你,我們得以前進,你的支持是我們的動力
更多文章
廚房水管發出臭味怎麼處理?內行人教3招消滅味道,同時能防蟲又防臭許多老屋或使用已久的管線都會有異味或是臭味的困擾,一名網友也因為深受其擾,因此忍不住在「我愛全聯-好物老實說」的臉書社團上發文詢問,表示租屋處的廚房水管真的臭到讓他受不了,對此許多網友都附和同意,「我的也是,廚房、廁所都有反味,每次洗澡時沖啊洗啊,第二天又聞到。」也有不少人回應原PO的煩惱,提出許多解決方式,以下綜合大概分為三種方法:
公孫策專欄:去貪是新總統首要之務 這個星期六就要產生下一任總統,三大陣營的攻防重點其實正是中華民國台灣最大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兩岸關係,一是政治清廉,其他議題都無關勝負。
觀點投書:民進黨造勢力攔狂瀾,仍沒留住年輕人的心民進黨4天3夜環島拼圖造勢剛落幕,立刻宣佈全台拜票行程,串聯817個路口造勢,從三組政黨的競選造勢活動上看,民進黨的造勢活動內容最豐富、形式最多樣。不過即使在造勢活動上大顯神通,力攔狂瀾,仍沒有留住青年選票。
政壇首位!柯文哲YouTube破百萬訂閱 流量第一名影片是這支2024總統大選倒數5天,擅長空戰的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日前開設「KPTV」進行直播,今(8)日傍晚他的YouTube頻道正式突破百萬訂閱,成為台灣政治人物的第一人。柯文哲得知頻道破百萬訂閱,仍平常心表示「繼續工作、繼續工作」,也希望在接下來的車隊掃街、廟口開講,更賣力讓選民認識他、把選票投給他。
台南殉職警察家屬問廢死看法 柯文哲:若我當選,不執行死刑就終身監禁2024總統大選倒數5天,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今(8)日到台南舉行民眾開講,台南殺警案殉職員警曹瑞傑的哥哥到場並向柯文哲提問對於廢除死刑的看法,柯文哲表示,台灣從來就不是個法治的國家,常常法律訂在那卻不執行;若他當選,對於死刑只有2個選擇,不是執行,就是修改法律為終身監禁。
侯康台中造勢喊10萬群眾相挺 盧秀燕拋磚引玉:為組聯合政府不進入內閣總統大選倒數5天,國民黨「侯康配」今(8)晚在台中市辦造勢大會,現場湧入10萬群眾熱情相挺。外傳若侯康配勝選,有可能會找台中市長盧秀燕擔任閣揆,盧秀燕今晚也明確表態說,若侯康配當選,將邀請其他在野黨成立聯合政府,她先拋磚引玉「不進入內閣」、「不接閣揆」,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更大的人事空間,與其他在野黨合作、共商人事。
侯康勝選將接閣揆?盧秀燕承諾不入內閣:媽媽要繼續留在家總統大選倒數5天,國民黨「侯康配」今(8)晚在台中市辦造勢大會,現場湧入10萬群眾熱情相挺。外傳若侯康配勝選,有可能會找台中市長盧秀燕擔任閣揆,盧秀燕今晚也明確表態說,若侯康配當選,將邀請其他在野黨成立聯合政府,她先拋磚引玉「不進入內閣」、「不接閣揆」,給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更大的人事空間,與其他在野黨合作、共商人事。
海外客家鄉親返台助選 力挺為客家人做最多事的許智傑總統立委大選本周六將投票,今(8)日由全球台灣客家信賴後援會-林敬賢會長、世界台灣客家聯合總會-鍾振乾總會長、北美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曾俊明會長率領的全球海外客家信賴助選團到立委許智傑的競選總部助陣讚聲,許智傑不僅高唱客家經典歌曲「客家本色」,更用客家話與現場鄉親寒暄,現場氣氛溫馨又愉悅。許智傑表示,客家在臺灣的文化中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人才輩出、各行各業都有客家頂尖人物;客家人堅忍、善良、樸實的特質,非常值得所有人學習。許智傑強調,高雄的客家分布,刻板印象都是位於大旗美地區,但其實隨著都市發展以及人口遷徙,現在客家鄉親最多的地方其實就是鳳山以及三民,並隨之發展出「都會客家」的型態,目前也致力修改客家基本法中,對於客家重點發展區的認定條件,希望藉修法,照顧更多都會客家的鄉親,協助傳承優美的客家文化。林智鴻議員表示,鳳山的客家鄉親人口佔有近20%,比例非常高!客家人的權益保障以及文化的傳承,是我們非常重視的議題,尤其許智傑委員提出的客家四大願景,包含「修改客家基本法」、「閩、客、原、新族群共榮」、「閩客共學」、「客家博覽會在高雄」,皆受到客家團體的力挺及支持。許智傑強調:「我雖然不是客家人,但非常願意推廣客家文化、學習客家語言,立志要當客家文化的模範生。然而本次選舉的對手打著客家後生的旗幟,卻背棄客家本色中的修好心田、實在踏實的精神,不僅在議會毫不重視客家議題、不出席客委會預算審議,更是以抹黑、潑髒水的不實資訊,意圖詆毀我的形象,實在是無法接受!呼籲鳳山的市民好友以及客家鄉親,一定要拒絕假消息的傳播,選擇最傑出、為鳳山做最多事的許智傑。」
中鋼去年稅前賺45.98億元 12月稅前淨利9.24億元、月減9%中鋼今(8)日公布去年12月自結數字,單月稅前淨利9.24億元、月減9%,相較2022年同期虧損已轉正;累計2023全年營收3633.26億元、年減19%;去年稅前淨利45.98億元、年減80%。其中,個體(非合併)碳鋼銷售量,12月碳鋼銷售量為610,273公噸;今年累計碳鋼銷售量為7,749,306公噸。
國民黨無論勝負,恐怕都會讓習近平失望!經濟學人:對中國而言,台灣大選是一場迫近的危機《經濟學人》的「茶館」專欄4日刊出〈台灣大選對中國而言是近在眼前的危機〉(ForChina,Taiwan’selectionsarealoomingcrisis)一文,強調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的賴清德如果獲勝、甚至國民黨在總統與國會選舉都遭遇慘敗,將讓北京懷疑台海兩岸是否還有「以協商達成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今年的台灣大選決定的不只是未來四年的台灣領導人,也透露了台灣問題能否「政治解決」、還是只有武力才能達成中國的統一夢。
趙少康提「1點1元」政見撼動醫界喊投藍 衛福部長回應了台大醫院醫師施景中7日在臉書發文,指出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少康日前開出健保給付1點1元的支票,對民進黨賴蕭配的殺傷力很大,甚至有醫界人士直言「今生第一次要投國民黨」;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辦公室8日則提出平均點值0.9元、朝「1點1元」目標邁進的承諾。對此,趙少康在臉書發文回應,有比較才知道好壞,並保證若是當選,絕不會辜負大家所託。
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請注意!新北失業勞工子女生活扶助金8日起受理申請 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請注意!凡家有子女就讀國內私立大專院校,經向勞動部申請「112-1學期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並獲審核通過者,可再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申請生活扶助金,最高可補助新臺幣1萬1800元,合併勞動部補助最高可達3萬5800元,完全比照軍公教子女教育補助標準。本項申請收件自1/8起至2/7止,提醒符合資格的市民朋友把握時間。
台中購物節網路聲量蟬聯3年全國第一 1/9抽出壓軸千萬好宅得主2023第五屆台中購物節已告一段落,活動每年均為網路發燒話題,根據網路溫度計以《KEYPO大數據關鍵引擎》輿情系統分析,這屆活動創網路聲量高達22萬3,250筆,相較前屆15萬筆,成長近1.5倍,且比第二名他市購物節高達20倍之多,再次榮登網路人氣最高購物盛事,為連續3年全國第一,台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表示,這屆活動開獎逾7萬5千名得主,9日上午11時將抽出壓軸千萬好宅得主,歡迎全國民眾將手機保持暢通,並可至活動官方臉書收看直播。
新北市公安小組加強百貨商場安全 春節前公安稽查適逢春節前年貨消費高峰期間,各大賣場及百貨商場等公共場所湧入大量人潮,為強化新北市各大賣場、百貨商場等場所春節前公共安全,今(8)日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李清安局長率新北市府工務局、衛生局及經發局等公安小組團隊,前往新北市面積最大之百貨商場-板橋大遠百進行公安聯合稽查,以維護消費者公共安全。
守護環境清潔 新北「柴」取行動 即日起拍照上傳抽好禮為推廣遛狗隨手清狗便,新北市環保局推出新北限定可愛柴狗便(袋)箱,提供飼主方便取袋清除狗便,目前轄內已增設至140座,環保局今(8)日特別在「新北i環保」Facebook粉絲專頁啟動「柴取行動,黃金不外露」活動,民眾只要依貼文指定步驟參與活動,就有機會獲得萬元禮券等好禮。
五月天3月高雄世運開唱 當年推手賴瑞隆:演唱經濟大爆發亞洲天團五月天宣布25周年演唱會,將於3月23、24、29、30、31日一連五月在世運主場館開唱。昔日邀請五月天擔任高雄城市代言人、高雄市政府前新聞局長現任立委的賴瑞隆表示,高雄演唱會經濟是從2009年五月天來到世運主場館啟動,後來邀請擔任高雄城市代言後,更年年在高雄跨年、舉辦演唱會,更在2013年五月天連趕夢時代、世運兩場跨年晚會,創新捷運日運量達47萬人次,至今紀錄高掛難以超越。賴瑞隆表示,2008年在市府觀光局擔任主秘時,因籌備高雄燈會藝術節,邀請五月天壓軸演出廣受好評。2009年高雄世運結束後,相信音樂評估籌備五月天世運主場館演唱會,和高雄市政府合作下,五萬張演唱會門票在48小時售罄,周邊交通配討規劃完整,讓國人朋友看見高雄舉辦大型演唱會的實力。
新竹台大歡慶3週年院慶 楊文科:期許早日升級醫學中心新竹台大分院今(8)日在生醫醫院竹北院區舉辦「逐夢飛越3週年:國際智慧醫療暨健康照護」院慶記者會,新竹縣長楊文科肯定余忠仁院長卓越領導,讓整併的3個醫院做很好的業務分工和資源分配,醫護細心照顧病人、守護鄉親健康,績效良好受地方肯定。楊文科也期待新竹台大醫院不斷茁壯,早日達到醫學中心的目標。
日本石川強震 中國信託送暖 中國信託銀行及日本子行東京之星捐款2,000萬日圓賑災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本(1)月1日發生芮氏規模7.6強震,當地多處道路斷裂、部分房屋倒塌,根據日本《NHK》8日下午報導,截至目前已造成168人死亡、輕重傷565人,並有323人下落不明,日本石川縣亦於6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簡稱「中國信託銀行」)及其子行日本東京之星銀行(簡稱「東京之星」)今(8)日宣布共同捐款2,000萬日圓,以實際行動送暖,協助災區重建工作,期盼受災民眾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蔣萬安呼籲選票集中支持李眉蓁!瑞豐夜市民眾沸騰大喊3號ok 高雄左楠區立委候選人李眉蓁,把握選前最後一個星期日全力衝刺,7日上午由幾位里長陪同穿梭街頭拜票;下午參加國民黨團結勝利大會;晚上和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台北市長蔣萬安在瑞豐夜市拜票現場沸騰,許多民眾大喊ok,國民黨勝利。李眉蓁表示,高雄起風了,在掃街的時候越來越多民眾勇於表態支持國民黨,這是勝選的先兆。在團結大會現場,看到十幾萬民眾來自四面八方,大家齊喊凍蒜,讓她非常有信心可以勝選!晚上李眉蓁和蔣萬安在漢神巨蛋美食節街用餐,許多民眾爭著合影,也比出OK手勢幫李眉蓁加油打氣。蔣萬安特別幫李眉蓁拍短片,鼓勵打氣;也呼籲民眾1月13日選票集中支持李眉蓁,要出來投票、顧票再幫忙催票,讓李眉蓁當選。隨後李眉蓁和蔣萬安市長到瑞豐夜市與侯友宜總統候選人會合,一起進入瑞豐夜市拜票,許多民眾爭相拍照。
飛機還在天上飛,機身卻破了一個大洞!737 MAX 9艙門破裂事故,讓波音再次陷入困境阿拉斯加航空的1282航班上週五(5日)發生艙門破裂的空中事故,雖然沒有造成任何嚴重傷亡,但這架737MAX9的乘客171名乘客(與6名機組員)確實都嚇出一身冷汗。畢竟正在飛行的客機機身破了一個大洞,任誰都無法在飛機上保持淡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也下令「完成檢整之前、停用部分MAX9飛機」。《路透》指出,雖然現在確認事故原因還為之過早,但這起事故確實讓波音公司再次陷入困境—因為737MAX的安全性問題再次浮出檯面。
合體藍營戰將台北街講 蔡壁如:將教科書等級翻轉選情台中市第1選區號稱是藍白合示範區,民眾黨立委候選人蔡壁如8日表示,對手民進黨立委候選人蔡其昌從躺著選到現在開始慌了,並稱她的選舉翻轉堪稱是「教科書等級的選舉」,一步一腳印,若自己夠認真,四面八方就會來幫忙,加上國民黨沒有提名,因此在野力量團結。
三鶯新生活啟航 再增5,249戶受惠污水接管服務新北水利局辦理「新北市三峽區、鶯歌區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工程污水管線第十標(次幹管、支(分)管及用戶接管)」,於112年12月29日決標,施工範圍為鶯歌區鶯桃路西南邊與德昌街附近區域、三峽區民生街以東及三峽河以北區,涵蓋鶯歌區永吉里、三峽區龍埔里,並沿鶯桃路及鳳鳴路建置污水次幹管通往鳳鳴重劃區,預計116年完成,5,249戶受惠污水接管服務。
批李柏毅論文抄襲又說謊 國民黨籲新潮流髒手從校園拿開民進黨左楠立委候選人李柏毅被爆論文涉嫌抄襲,李柏毅宣稱2013年就通過圖靈系統比對。今天國民黨由副發言人呂謦煒、市議員陳麗娜共同召開記者會,公開質疑李柏毅跑出13%相似度的版本為畢業後修改版或疑似造假。國民黨表示,高雄大學在2020年才引進圖靈比對系統,顯然李柏毅抄襲又說謊,人格完全破產。此外,據傳高雄大學周日緊急擬定為李柏毅辯護說帖,懷疑新潮流把黑手伸進校園,逼校方做出有違學術倫理之事。
今日新聞頭條》2家媒體成政黨打手?黃珊珊大爆料:電視台總裁要他補選新北市長距離2024總統大選倒數,各政黨最後出招機會僅剩下最後5天,民進黨近期因為有間電視台因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不願賣廣告,因此綠營就指控侯友宜控制媒體。不過,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則認為,當年民進黨說黨政軍要退出媒體,結果7年後的今天,黨政軍就是媒體。黃國昌更直接點名2家電視台:《東森電視》變「東森侯侯台」、《三立電視》變「三立打手台」。黃珊珊更加碼爆料東森新聞台總裁給她三條路可以選,這是怎麼一回事...今日新聞頭條《風傳媒》帶你一次看懂。
林口運動中心「一箭穿心」兒童傳統射箭冬令營帶孩子培養專注力寒假期間送孩子參加運動中心冬令營好處多,除了養成規律運動習慣也能接觸多元運動項目。林口運動中心於寒假推出「金牌運動會」冬令營隊,規劃各類單項運動營隊,包括籃球、羽球、桌球、壁球、空氣槍、傳統弓箭、日式劍道、飛盤、樂樂棒球、跆拳體能、流行街舞、游泳等,今(113)年全新推出撞球營隊及扯鈴營隊,參加營隊讓孩子們探索或是進一步學習喜愛的運動項目,體驗各項運動的樂趣。
賴清德喊話守住左楠李柏毅 李柏毅送上全糖珍奶致謝民進黨今(8)展開全國大車掃,賴清德與蕭美琴南北兵分二路,力拚各地立委選情。賴清德中午至左營楠梓陪同立委候選人李柏毅車掃,李特別奉上全糖珍奶,賴清德見狀後更是開心收下。昨日鳳山造勢時,賴清德亦強調左營楠梓是最激戰的選區,呼籲鄉親禮拜六走出家門,用選票守住高雄最關鍵的一席。
高雄車站遺構化身記憶牆版!展示歷史紋理 述說咱的故事隨著2021年高雄驛帝冠式車站的賦歸,代表高雄城市新願景的啟動,而當年為了遷移局部切割拆除的車站牆體遺構,如今也以「歷史記憶牆面廊道」方式展示及保存於高雄車站東側綠園道上,後續園道內除了提供市民休憩運動環境,也融入歷史性城市美學及穿越性道路,更結合周遭自行車道路網,藉以串聯周邊商圈、活絡商業發展。
黃金週到三民區力挺李昆澤 賴清德:李是最有經驗與方向的交通立委距離選舉僅剩五天,今(8)日賴清德來到高雄市為第五選區(三民區、苓雅八里)立委候選人李昆澤助選,兩人一起車輛掃街,向民眾揮手致意、全力催票。兩人合體車掃獲得許多民眾熱情回應,在路邊揮手、搖旗、高喊「凍蒜」、並舉高手比出「2」的手勢,為同為2好的賴清德與李昆澤加油打氣。
55歲袁惟仁成植物人!最新現況曝光,紀寶如曝:已經認不得人了資深藝人紀寶如熱衷公益,目前擔任台灣優質生命協會秘書長,長年關懷獨居長輩,和演藝圈內的老藝人。近日出席餐會時,紀寶如坦言音樂人「小胖老師」袁惟仁2018年在上海腦溢血病倒,加上2020年在家中摔倒導致頭部重傷,目前生活起居無法自理,且意識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