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本文學評論家而言,以現今的時點或者立場,去評價一名活躍於八十餘年前日本文壇的作家,必然存在著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嚴肅考驗。首先,論者必須冷靜自持看待其所有作品,尤其在思想性與藝術性的優缺點。其次就是,不因同情或支持其政治主張而放棄批判,更不能畏於已由其黨派樹立的文學權威地位,輕易隨之附言,因為任何預設性的既定評價,一開始就已經自失立場了。
以《防雪林》、《蟹工船》、《在外地主》、《工廠細胞》《為黨生活的人》等小說聞名的小林多喜二(1903-1933),即是最佳的例證和挑戰,因為其作品有對於時代的控訴和對於弱勢底層者的同情,而這種描述又很容易將我們推向道德領域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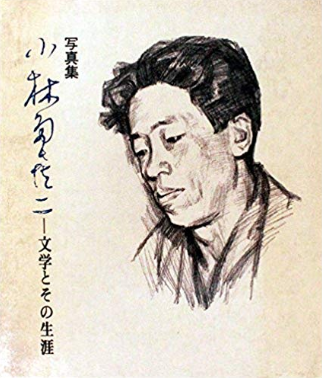
從文學啟蒙到憤怒青年
基本上,小林多喜二的文學創作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他於1918年就讀小樽市商業高校時,擔任校友會雜誌的編輯委員,已經開始發表和歌、新詩和小品文。1920年,他們編製手抄的傳閱雜誌《素描》,這個刊物即這些文藝青年的發表園地。他們同仁之間彼此約定,每月都要閱讀《文章世界》和《新潮》雜誌,並且鼓勵向這著名刊物投稿。他就曾向《小說俱樂部》《新興文學》等雜誌投稿。
這個時期,日本的出版界已開始大量翻譯和介紹俄國和西歐的近代文學名著。譬如:俄國杜思妥也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罪與罰》、屠格涅夫的《初戀》以及義大利詩人鄧南遮的《死的勝利》、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和法國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等,可謂迎向世界文學的時代。
在這文學思潮的刺激下,日本文壇亦催生出相應的作家和作品,如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秋田雨雀的〈國境之夜〉、江口渙的《惡靈》、小川未明的《紅色地平線》、有島武郎的《一則宣言》、倉田百三描寫親鸞和尚的劇本《出家及其弟子》、賀川豐彥描寫在神戶貧民窟富有傳教體驗的小說《越過死線》、島田清次郎的長篇小說《地上》,等等。毋庸說,這些作品自然成為當時文青們文學養份的來源。只不過,這些帶有感傷情調的作品,終究缺少深刻的思想性。
關於這個缺點,小林多喜二在〈新生的孩子〉一文中,亦有明確提及:「在這以後,我寫了不少拙劣的作品,只是在我心裡,總有一種要和過去作品訣別的心情。當然,這對我來說,應該是一件高興的事情,並不意味著在貶低以前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幼稚,但它是過去的我——至少是形成現在的我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希望諸位讀者能夠多加包涵。我期待讀過這兩篇小品之後,把您所感覺到的一切毫無保留地寫下來,因為不管好壞,它將成為我今後前進的路標(參見手塚英孝《小林多喜二傳》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